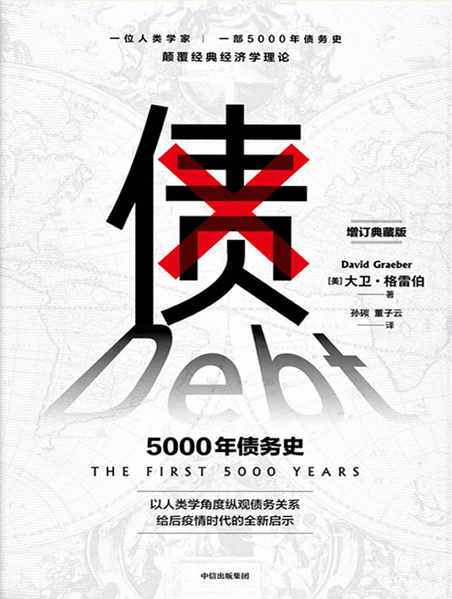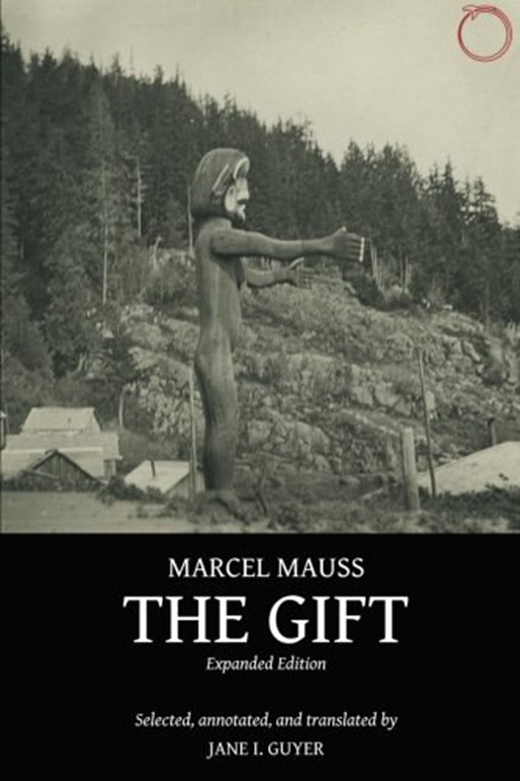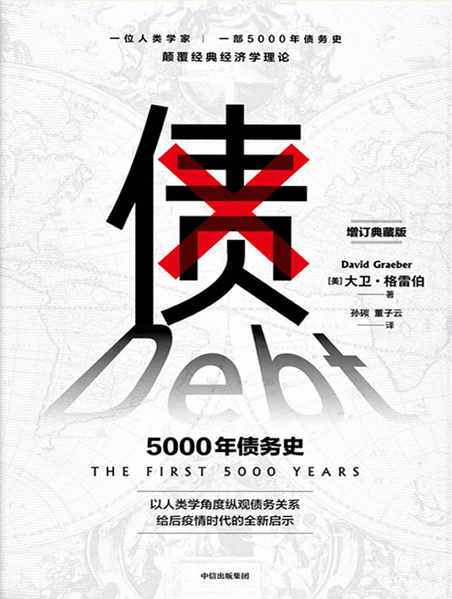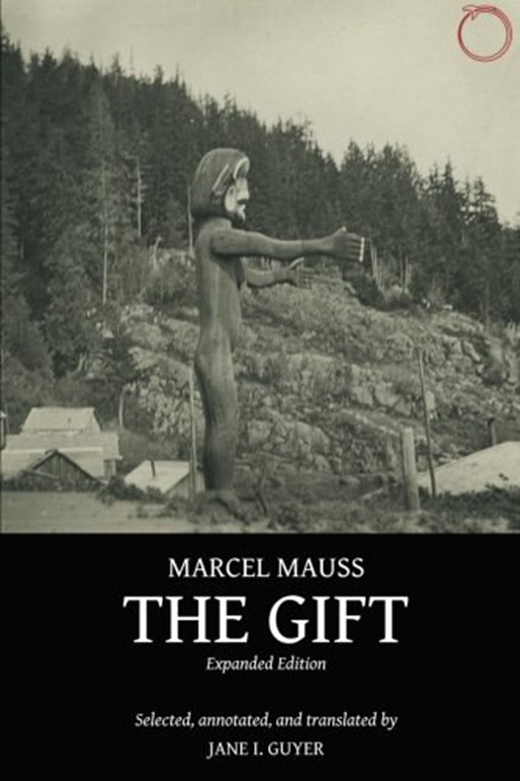“欠债还钱”这一基于道德困惑的经验是格雷伯书中论述的起点,这个常识性的观点在经济学的债权人风险理论下看似是不成立的,在中国的语境中这个口语化的表达往往与“天经地义”的后缀一同出现。当“还债”作为一种不言而明的“经义”,它就不再属于单纯的经济学范畴,而成为一个道德层面的论述。这正是格雷伯在《债》一书中的核心问题:现代经济和市场化将道德感和正义感简化为商业的表达方式,这意味着可以被量化和精确说明的债务取代了原始的道德责任,这一趋势裹挟着暴力、国家和市场,通过战争、奴役等方式抽离掉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格雷伯论述的基调是对现代经济学“以物易物”交易关系和资本主义运作模式的批判,他在文中提到的“共产主义”、“交换”和“阶层”原则成为道德逻辑的基础,这也回应了莫斯在《礼物》一书中的观点:给予的义务、接受的义务和回报的义务构成的礼物交换制度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送与取”,而这也正是社会道德逻辑的源泉。不仅如此,两位学者在书中的许多观点都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试图唤起共同体原有的道德、宗教和社会的一面。格雷伯批判的谬误之一就是作为经济学核心的“以物易物”神话,他拒绝把人类之间的所有关系都简化成交易表示,这来源于他与斯密关于人性的不同假设。斯密认为经济生活的基础就是人性中的一种必然习性,“交易、以物易物、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习性”(格雷伯,2021:46)。格雷伯将人性的基础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础,指出看似是伦理学基础的“互惠性”并不是真正的正义,不仅无法解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道德关系,反而可能导致“以牙还牙”的暴行(格雷伯,2021:139)。他将“共产主义”、“交换”和“阶层”作为人类社会主要的道德原则,也是经济关系形成的基础。“共产主义”在此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财产分配制度问题,而是一种道德原则。他强调的不是消灭私有制回到集体资源共同管理状态的“神话共产主义”,更大程度上是社交性质的“底线共产主义”。这里作者的论述与莫斯对夸富宴的描述非常相似,“礼物的馈赠与收取,通常都明显带有比赛的性质,一般是实际的比赛、竞技、盛会和表演的延续,而这些通常也代表宴会的受欢迎程度。对于社会整体来说,分享的欢宴能够被看作某种共产主义的基础。”(格雷伯,2021:148)这也正是莫斯论述的夸富宴作为社会形态学现象的特征,不同部族和家庭等在夸富宴上集会,造成了强烈的紧张和兴奋,正是在接二连三的竞赛中人们互相沟通或彼此对立(莫斯,2016:61)。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的基础不是交换,也不是互惠性,而是包含期望与责任的道德逻辑。“交换”与“交易”仅有一字之差,但是在格雷伯的论述中却有根本性的差别。交换的核心是平等,但这种平等是充满张力和动态的,“并不存在精确的对等,而是倾向于实现平等的持续互动的过程”(格雷伯,2021:154)。而交易中的平等是钱货两讫的,这种看似绝对公平反而抽掉了交换中的道德意涵。交换的张力通过竞争的因素来展现,这又与莫斯夸富宴竞争和对抗的原则相联系。交换会变成比拼慷慨的物质竞赛,每个人都会炫耀谁能馈赠的更多(格雷伯,2021:155)。正是这种竞赛使得礼物处于一种无尽的循环状态,通过这种方式社会被建立起来。格雷伯在阶层的论述之后引出了债务的本质:“在平等的双方之间的这种协议,使得双方不再平等(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平等)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正是‘债务’的本质。”(格雷伯,2021:177)当债务没有被偿还的时候,阶层的逻辑就发挥其作用,进一步打破了互惠性的假设。无法偿还的债务,尤其是作为荣誉的债务是个人的危机,这也正是贵族吸引追随者的方式,是莫斯所言夸富宴的背后深意。而现代经济学中的交换在平等中也隐含着分离的倾向,当量化的债务被取消,双方的身份就被拉平,不再具有任何联系;而债务的微妙之处在于,双方伴随着平等的可能,由于持续“不平等”的创造而不断互动,这种建立在债务之上的责任正是道德社会的基石。没有债务的世界将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毫无关联和责任的存在,当人性的道德逻辑被剥离,剩下的就是量化的身体而已,“我们都将变成孤立的行星,甚至无法指望能够保持在合适的轨道上运行。”(格雷伯,2021:186)格雷伯在挑战经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阐述了经济关系中的道德基础,之后他系统的回顾了从轴心时代到1971年之后不确定的时代货币、债务等发展的历史,总的来看关于债5000年的历史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部“关于信用经济如何转变为利息经济、非人格的国家权力如何侵入并改变道德网络的历史”(格雷伯,2021:472)。当今时代的债务货币化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货币的本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交换媒介,仅仅是一种价值尺度,格雷伯用了一种更激进的说法阐述货币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角色:“货币没有实质,它事实上什么也不是,因此本质一直是,而且估计以后也仍然是政治争论的问题。”(格雷伯,2021:525)典型的例子是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出现,这是阶级斗争调解的一种方式,其实质是政府与工人阶级的交易,通过享受广泛的社会福利搁置可能改变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这正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凯恩斯时代”,在此背景下银行可以通过凭空造钱来刺激需求;而现实是工人们被刺激需求,“金融的民主化”让人人都可以成为食利者,由此发展出的新自由主义使得资本主义成为一切事物的组织原则,结果是格雷伯所言的荣誉原则几乎完全从市场中消失了(格雷伯,2021:530)。格雷伯在后记中提到自己最大的灵感来自莫斯,他揭开了作为现代经济学基础的有关人类生活和人类本性的真相,试图为“以物易物的谬误”提供另一个选项(格雷伯,2021:553)。格雷伯和莫斯都强调了所谓“经济生活”的道德逻辑,在《礼物》中,人是通过物与精神的融通来实现社会的融通的,“hau”作为物之灵,为社会提供生命的源泉,使得个体不再是孤立的状态,而是不断的处于给予、接受和回报的义务之流中。而西方社会的道德危机和社会团结危机就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将个人权利与物权、人与物截然分开的社会中”(莫斯,2002:137)。格雷伯的论述也最终落脚于此,经济的历史归根结底是道德的历史,贯穿着共产主义、交换和阶层的道德逻辑。“债务是对承诺的曲解,是一个被数字和暴力腐化了的承诺”(格雷伯,2021:548)。作者最后在对现代社会债务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学家对自由的展望,真正的自由是做出真正承诺的能力,是社会交往中的道德性行动。这正是他作为人类学家对社会的关怀与体悟,经济学家倾向于在数学模型中假设人性,围绕数据与方程式组合历史,而历史学家依赖经验主义拒绝作出自己的判断,只有人类学家,正如格雷伯所言,“被完美地安置于此”去重新思考对经济历史律动的认知(格雷伯,2021:551),从中可以一窥人类学的特色与关怀。格雷伯在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系的办公室。潘佛华摄于2020年9月

大卫·格雷伯
大卫·格雷伯,2021,《债:5000年债务史》,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马赛尔·莫斯,2002,《礼物》,汲喆译,陈瑞桦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