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内绿树成荫,芳草连绵,教学楼似乎也比往日更加肃丽,一袭袭黑色长袍在 其间流动,一顶顶学位帽时而跃至半空,流苏垂落随微风轻摇,如花笑靥与阳光交映。相机随处可见,毕业生们嬉笑成群,流连在各个景点打卡拍照。以上,只是毕业季的寻常校园风景。从论文答辩、毕业典礼、送别聚餐、留影纪念到学生晚会……一系列仪式在毕业季重复上演,届届学生在体验类似的话语、行为和活动。毫无疑问,毕业仪式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意义,对于这一已被内化的大学结束程序,我们如何利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它是如何具体实现其功能,传达其意义?对于中国大学生的人生阶段意味着什么,又有着怎样的文化特殊性?
毕业仪式的英文表述是Commencement,既有结束,又有开始之意,和学理层面“通过仪式”的内涵不谋而合。现代高等院校的毕业典礼传统源自12世纪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此后渐渐成为欧洲学府的年度盛事。哈佛学院在1642年举行了北美的首次毕业典礼。毕业生的学术礼服(academic costumes)承袭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习俗。人类学家范·杰内普从“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系统考察了人类出生、成人、结婚、死亡等人生过渡阶段,认为“通过仪式”标志和促进人类从一个阶段的存在状态转向另一个阶段的存在状态,是伴随每一次地点、状况、社会地位以及年龄的改变而举行的仪式(1909)。范·杰内普还首创了仪式的分离、阈限和再整合三个分析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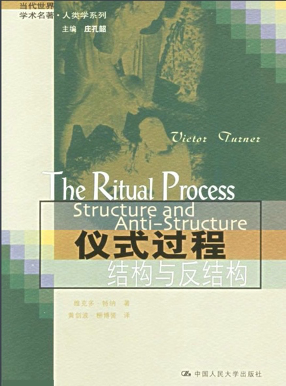
一、分离
分离(separation)阶段是参与者从原先处境或整体的文化形态中剥离出去,开始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转移。对应的是毕业季中关系的逐步松解。学业上学位论文答辩结束、修读计划完成,政治组织关系的脱离,借阅图书的归还,财务状况的清算……毕业生与学校原有的归属关系一一松解、脱离,成为无归属的客体。由于本科四年学生与学校嵌入的面向之广、程度之深,分离的手续、步骤和历程也更为漫长,在进行时间上一直延伸第二阶段阈限的中后期。与此同时发生改变的是,毕业生逐渐摆脱学生身份,不再享有学校的组织庇护而成为社会上独立存在的个体,即使准备继续升学,也会意识到其社会角色,是时候该真正长大了。
二、阈限
转移或阈限阶段是指仪式参与者已离开原有社区,但又尚未进入新社区的中间的暂时性悬置阶段,这一阶段仪式主体(passenger)的特征并不清晰。对于毕业典礼来说,转移或阈限阶段占据主要地位。如上文述,从结构和交融的分析框架出发,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子模式,其一是基于结构性关系的阈限模式,以操作化的仪式为表征,典型表现为校方举办的毕业典礼,其二是超越结构性关系的近阈限模式,仪式的表达更灵活多样、选择余地更丰富广阔,人与人的关系平等而交融甚至是倒置了日常的社会差别,表现为弥散性的学生晚会、喝酒聚餐、拍照留影等。
(一)结构性阈限
在结构性的阈限阶段,毕业典礼是毕业仪式中象征和符号的浓缩。开始举办时放奏的校歌,是师生们集体记忆的载体,在传达集体情感的同时提醒着毕业生作为校园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接下来,是共同体成员代表发言,从校长、优秀教师、杰出校友,再到优秀学生,代表们各自以鲜明的身份地位带领观众们分享经历、重温过往。这类演讲具有类似氏族长老在篝火旁回溯古老传奇的功能,在再现重要故事和论述哲理中稳固成员联系,同时强化内部秩序和道德意识。以校长讲话为例,作为高校行政的最高主管,校长一方面会表示祝贺和追忆难忘的集体经历以引起情感上的过共鸣,另一方面也从集体价值、习俗、态度、感情以及关系出发,强调成员在步入下一人生阶段时该有的责任和担当,尤其是超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家国情怀和社会使命,因此这一阶段实际上也是毕业生社会化的历程之一(向伟等,2018)。和中国高校意识形态分明不同的是,美国精英高校则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强调要为全人类的福祉殚精竭虑(华维勇,2010)。

典礼的高潮是拨穗、颁证和赠礼环节。穿着富有象征意义的毕业服的毕业生迎来了属于他们每一个个体的出场机会,这一过程也是阈限阶段与再整合阶段的零界点(threshold)。处于阈限阶段的仪式主体是不清晰不稳定的,在仪式过程中,他们没有差异甚至是性别差异地被“通过”。作为“通过者”,他们是被动温顺的,处于结构关系中的低等级一列,而经过这一环节,他们将完成身份转换和地位的获得。从毕业服说起,因为现代高等教育起源于西方,由中世纪大学演变而来,因而有着深厚的基督教背景,学位服也是在牧师袍的基本架构上改进而来,意旨是代表着思想的成熟和独立的判断力,是学者身份的符号象征。又至中国近代,长袍马褂、长衫等向来是“文化人”、“有身份的人”的象征,因此,在表意符号体系上与西方近似,同时中国高校起初旨在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理念和西方也不谋而合,因此学位服也沿袭了西方高校的设计,只在局部细节,如前胸纽扣采用中国传统的“如意扣”,袖口处的长城城墙线(毛新青,2010)。学生们穿上学位服,能很好地体现出文化人、知识人、甚至是学者的气质。不过仅仅是穿上学位服,尚未正式获得身份的认可,处于低等级的毕业生,需要得到来自更高等级的代表的认可和准许,身份才能被确立。这一仪式过程就是拨穗礼节。
学位帽是形状如一本薄书的方形平顶帽,当被方方正正耸立在头顶之上时,自然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息,象征着学识渊博。学位帽的流苏则像丰收的稻穗,象征着学业期间的丰硕成果(毛新青,2010)。拨穗的主体方是校内的学术权威,往往由校长院长、系主任和杰出导师进行,在学位未获得之前,流苏垂挂在学士帽的右前侧中部,毕业生作为被授方,沉默而顺服地由导师将流苏从右边拨到左前侧中部,稻穗或麦穗象征成熟,这一礼节寓意毕业生们已经学有所成,完成之后才能合格地获取学位证书。这一礼节前,毕业生作为受礼者,仿佛如一块白板,拨穗授予了他们新身份的知识和智慧,他们的接受和顺从一方面代表着原先在校生的身份已经不复存在,一方面代表着其气质正在被调和。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是由社会所赋予的(特纳,1969:104)。而作为拨穗的施授方,因为交融的普遍性,他们也会有因人类本身的情感产生的心理感受,不过他们的权力主要来自于社会结构的职务任命,只是按照权力行事。而这种社会权力不仅仅来自学校共同体本身,更代表了崇高的、普遍性的学术和科学共同体,因而具有某种超自然和超人类的神圣性。

接下来是赠礼环节,已经获得了新身份的毕业生,将为校领导献上独立制作的纪念礼品,如书画、校园模型、印章等。这一礼节,表示了毕业生能以独立的社会地位反馈母校,同时也意味着毕业生与母校将绵延关系和情谊的连结,达成长期互惠互助的协议,正如复旦大学2020届毕业MV原创歌曲《有光》的歌词所示 “我身上有你的光,带着它我去远方,飞翔,飞翔,我乘着你的翅膀;你身上有我的光,无论我身在何方,照亮,照亮,汇聚成你的模样”, 母校与学子之间是互惠互助的荣誉共同体。随后的杰出校友和校领导发言,将更着重展望未来,敦敦教诲步入社会后的行为规范和处事原则。至毕业典礼结束,毕业生在系列的等级次序、结构分明的关系中正式而完整地实现了身份和地位的转变。
(二)交融性阈限
近阈限中,仪式的表达更为开放,活动选择余地也更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跨越国别、身份、地位、等级的结果差别,出于人类纯粹的共有情感和心理体验产生连接和实现交融(拉丁文communitas)。交融,即反结构的范畴,可以引入所有对抗性的行为之中,尤其通过戴面具、改装扮、可预见的无序行为而为自己改头换面的做法。在特纳的诠释之中,以颠覆性力量为诱因的行为本身,就是文化的基石。因为在这些行为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过程之中,产生了开放和改变的可能性,而这种开放和改变的状态就是日后所称的“虚拟世界(subjunctive worlds)”。就学校而言,中国高校隶大多直署于教育部,而毕业典礼中也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除了国家和民族意识,也突出学术和知识的崇高性,从而一定程度上抵制和消解了国家与社会的逻辑(程天君,2009),如复旦大学原校歌中所倡导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此外,大学校长的毕业演讲也不完全是居高临下,而会更贴近学生生活,灵活多变、主动吸收学生间流行的网络用语,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并且其讲话内容也一定程度上受到网友点评的限制(高丽蓉,2015)。
除了校方和上层领导的交融体现,交融关系在学生之间更常见和普遍。和毕业典礼中相对上级的个体无差别不同,交融模式中阐述的是相对成员内部而言的结构无差别,每个毕业生都是卑微与神圣、同质与同志的混合体,是仪式中“时间之内或时间之外的片刻”,以及世俗的社会结构之内或之外的存在(特纳,1969:96)。无论是毕业红毯、学生晚会、拍毕业照、毕业旅行还是朋友圈公示,毕业生们之间关系平等、经历共通,一些反常的行为也会被社会默许,如学生时代不被公开允许的喝酒聚会,中山大学流传数十年的异性集体“喊楼”示爱行为(黄志辉,2011)。这些集体狂欢和交融行为往往带有夸张和表演成分,或许是因为仪式之后,他们将被种种规则和秩序约束,难得再有放纵自我和天性的恰当机会了。
三、再整合
再整合阶段是参与者完成仪式后,以获得的新身份重新进入社会。仪式主体重新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状态,既有明确定义的、“结构性”类型的权利和义务,又需要承受新社会处境中的习俗规范和道德标准的期待。中国没有正式的成人礼(Initiationrite),本科毕业典礼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类成人礼的功能,毕业季的系列仪式让毕业生社会化,意识到作为成人的责任,更好地过渡到社会人。个体人生经历的时间是连续的本没有节点,毕业仪式作为意义的载体,促进了中国学生从在校生到校友、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过渡,象征着个体阶段性的变化。在校生通过毕业仪式,或系统性地总结反思回顾大学四年的成长与收获,或在仪式中梳理和巩固了亲情、友情、同学情等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或增强了对学校对班级集体的认知,为下一阶段铺路。末了,毕业生们带着记忆,以母校校友的身份,开始下一段的新生活。
四、结语
本文基于通过仪式的过程理论,解读了毕业仪式对于中国现代大学生的重要象征意义,在中国语境中,毕业仪式除了象征学业阶段的完结,还承担了类成人礼的功能,是以促进毕业生的社会化和成熟。经历了具有生命过渡仪式功能的毕业典礼,毕业生象征性地完成了其接受教育和服务对象到社会的给予者的专业身份的转变。毕业仪式的阈限阶段既包含结构性模式,也容纳交融性模式,并且随着中国社会环境开放性的增强,交融性关系将越来越被认可和接受。不过,与特纳突出呈现交融性模式对结构性关系的颠覆不同,中国毕业仪式中二者模式和谐共处,交融性关系并无意挑战结构性关系,而结构性关系也充分尊重交融性关系。
2020年的突如其来的全球化疫情扰乱了人类一切生产和生活活动,本该如期举行的线下毕业典礼也被取消。不过线上“云毕业”的形式和花样却层出不穷,可见人生转变产生的种种感情,离不开通过仪式来进行秩序化传达。从涂尔干的理解来看,毕业仪式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和社会意义,是集体意识的表达。共同体成员通过参与特殊仪式,巩固与同一成员内的彼此联系,建立和再现集体身份,创造与重温集体记忆,同时融合共同体特色,展望未来。在仪式表达中,代表人物完成一系列象征活动。过去和未来在此刻的仪式中交会,人们一起经历欢声笑语和伤感流泪,在情绪的起伏中集体团结被实现和稳固。此外,通过仪式还具有化解危机的功能,由学校和社会之间互相矛盾的社会规范所导致的危机,可以通过富有象征意义和内涵的仪式化解(特纳,1969:13),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双方之间促成和解(特纳,1969:20),比如毕业仪式通过渲染“过渡”本身的欢愉来暂时性忽视校园和职场之间生存逻辑的差异甚至冲突。因此,即使受多种因素阻隔,人们仍旧在特殊而艰难的境况下举办线上毕业仪式。

从线下毕业典礼到线上“云毕业典礼”这一场域和形式转变除了技术提供了可行性外,也充分体现了人类的应对智慧。通过仪式的理论让我们就仪式本身进行了充分的理解,却未能解释仪式形式本身的变迁。可以进一步思考,除了疫情等偶然性因素外,是否存在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因素促成通过仪式形式本身的变迁。
作者 |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2016级本科生 周克琳
参考文献:
维克多·特纳著,1969,《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志辉,2011,《“喊楼”:阈限中“羞”的释放——对大学生毕业仪式的一个剧场分析》,《当代青年研究》第8期。
杨成胜、李思明,2009,《交融 :在结构中闪光———对特纳“阈限交融 ”思想的再诠释》, 《世界民族》第1期。
毛新青,2010,《高校毕业典礼的文化人类学解析》,《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6期。
程天君,2009,《身份的转换:毕业典礼的学校逻辑》,《教育社会学研究》第1期。
向伟等,2018,《毕业典礼中校长讲话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基于 2017 年 150 所高校毕业典礼校长讲话的研究》,《长沙大学学报》第1期。
华维勇,2010,《中美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之差异分析—以近年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 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辞为例》,《秘书》第2期。
Arnold Van Gennep,1909,“The Rites of Passag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eville, Gwen Kennedy. 1984. “Learning Culture Through Ritual: The Family Reunion.”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15(2):151–66.
编辑 | 朱彦珺
图片来自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