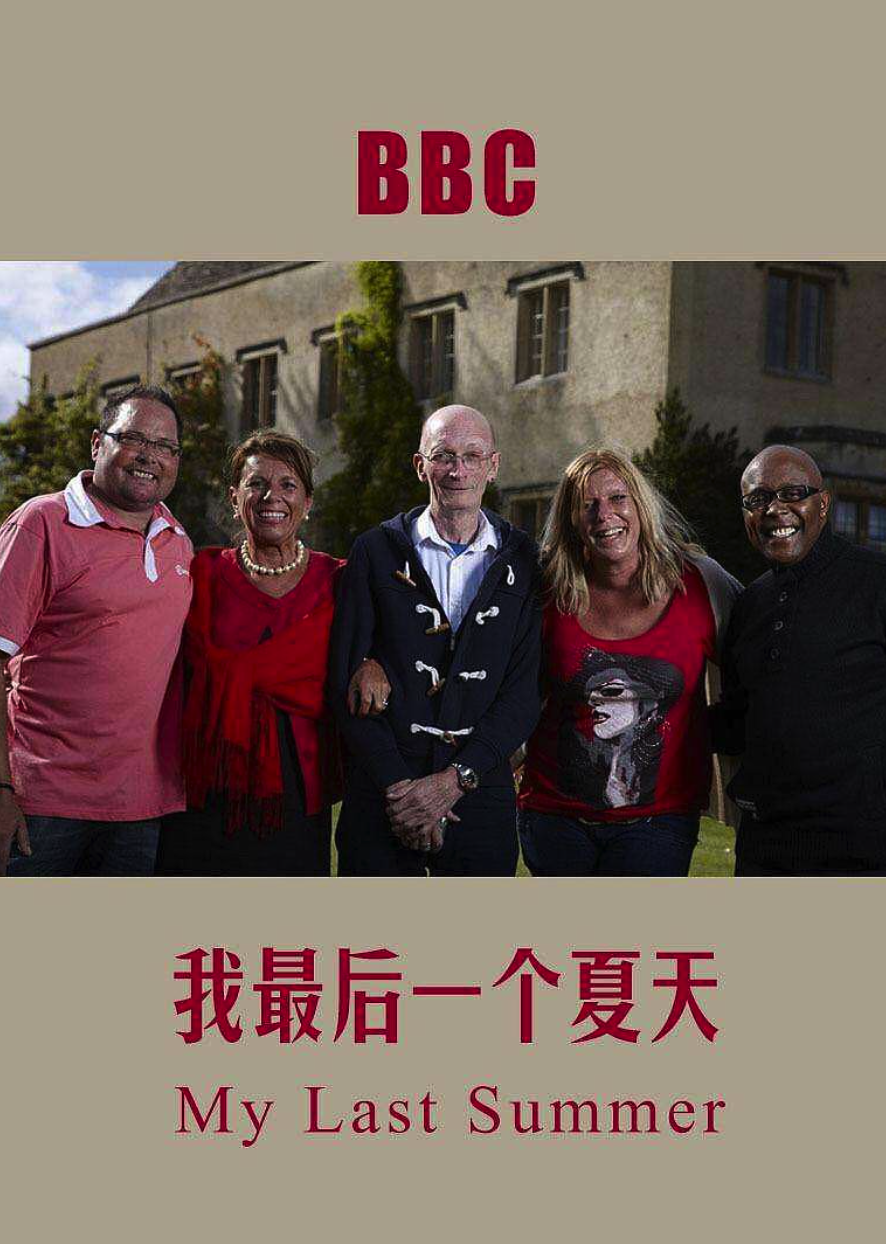
《我死前的最后一个夏天》(My Last Summer)是一部由BBC出品的4集纪录片,主要围绕五个被诊断为绝症,只有大约一年可活的素未谋面的38-58岁的病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四次会面拍摄,其中主角们坦诚地探讨了绝症的痛苦、死亡与亲密关系、对死亡的看法和身后事的打算。五位主角中:朱尼尔患已扩散至肺与骨的前列腺癌,他作为DJ潇洒一生,一年半前终于恋上想要长久相伴的女友索尼娅,但病中却像一个乞求她的照顾的孩子;珍的一生都在尽量为他人着想,直到被诊断为乳腺癌时的她的丈夫冷漠的反应击碎了她,她毅然断绝了二十五年的“美满婚姻”,由好友照顾,要求能够有尊严地离开世界;本,一个得肺癌的老头,在因病被辞退前一直在轮船上工作,没有自己的家庭,朋友也多半不在陆地上,准备好了形单影只地死去,甚至已经安排好了遗产和葬礼;安迪在生意破产为了省钱没有买健康保险的那一年得了白血病,最后丧失免疫、肺部感染,在病中无法正视家庭经济状况,也不愿告诉女儿真相;露得了黑山症,她告诉了子女与丈夫,但他们尚未能够真正消化。

本影评中许多内容涉及生死,但主角们,至少在拍摄时,仅仅是被诊断了严重疾病。此中似乎确实包含着某种疾病等同于死亡的不恰当逻辑,但此处不准备大量探讨这样的判断宿命论与否的问题。以下按他们确实会在较短时间内因病而死探讨。
一、合作的死
较之强调死亡的为他性、社会性和伦理意义的东亚文化,西方的死亡哲学更注重个体性、属我性、不可替代性。即便如此,My Last Summer中的五位主角的死亡远非完全个体的。他人左右着患者像钟摆一样徘徊不定的一把断头铡,他们的死念;患者的病重与死亡,不同地对生者的生活留下烙印。
1.死亡阴影下的互惠关系
身体极为虚弱的人很难离开他人的照顾。“病患”一词本就在文化上意味着社会承认这个人不能完成自己正常的任务,需要一些措施来特殊应对。[1]本片中,除了形单影只的、尸体被送餐服务者发现的本,四位绝症患者的陪护都是自己的亲人朋友。他们的身体状况决定了他们没有足够的活力,无法继续扮演一般情况下的丈夫、妻子、朋友的角色;有一些朋友直接因绝症离开了(Somebody just takes off),露的最好的朋友就“不能接受”她时日无多的事实,与她断了联系。对于留下来照顾自己的亲朋,绝症患者会产生一种亏欠、愧对的感觉:安妮特说安迪得病之后对别人更友善宽容了;朱尼尔说他感到难受,因为他希望索尼娅是以伴侣的身份而非陪护的身份留在他身边,如今索尼娅却像是他的母亲而非恋人。
亲友在提供病人必须的照料之外,更重要的影响是使得患者有一定的情感寄托,从而有不舍和继续生存的意愿:珍离婚之后,朋友阿黛尔就成为了她最强的情绪支柱。本最初认为拒绝做更多化疗,但是在认识了四位绝症朋友后同意了加倍化疗。索尼娅说,朱尼尔总是说如果没有我他早就死了。安迪说,如果不是安妮特,他不会在这里了。他们或许会为此有一定的感激,但同时,疾病的疼痛和心理的折磨使得这些慢性病患有时真正想要得到解脱而不是继续呼吸,比如My Sister’s Keeper中的凯特想要死亡,本片中朱尼尔和珍都会时不时说不想再活下去。这时所爱之人的期望就成为一种压力。
他们的亲人朋友为什么留在他们身边,没有抛下他们?安妮特说她也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白血病占满,但既然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她理所应当会照顾他,他们是一起的,没有别的办法。索尼娅说当你爱这个人,你就会这样做;你会觉得自己痛苦,但想起病人,他们痛苦更多。前者的描述类似于,由于婚姻关系,照顾病人已经成为了一种无法逃避的“义务”。此处的互惠是一种对捆绑关系的确认,[2]防止失去这一种捆绑关系带来的内心的煎熬和可能受到的社会谴责。后者同样可以说是确认伴侣关系,满足社会认可、内心安宁。同时,亲人会担忧自己不希望患者死亡,要他们受尽折磨地活着的念头是自私的,但在他们的付出之下,许多欲死患者会为此做出让步,展现出更多的求生欲。
总而言之,在亲人朋友陪护者与绝症患者的互惠关系中,前者提供几乎舍弃自我生活的、全心全力的照顾看护,并作为情感寄托为患者带来心理安慰;后者客观上为前者提供了安稳踏实,主客观上都回报前者以牢不可破的捆绑关系与爱,有时以自己努力坚持配合治疗、活下去作为回报。更大程度上是亲属的泛化互惠;但如果患者本人确实已无求生欲,但陪护者需要他生存下去,使得患者出于亏欠之感选择坚持,就有更浓重的平衡互惠色彩,即便常识上保持生命是自利的。
2.自然生命死亡之外
病人对于自己自然意义上的生死的决断已依赖于很多社会因素:亲人的挽留、法律因素的限制、宗教信仰的规劝……病人本身,尽管曾有争议,目前似乎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为具有死亡权,因为生命的结束并非简单的生本能对死本能的胜利或自然因果律对自由因果律的胜利, 而是一个死本能和生本能通过相互否定、相互超越而达到的二者共同完成的终结状态,死亡是生命的内在本质,死亡权是生命权的应有之义。[3]
但除自然层面的死亡之外,对于其社会意义上的消失,患者似乎更加无力。慢性病人,相比起意外离世者,在诊断之后、去世之前,长久地活在生死之间:生物意义上,他们仍然活着,葆有自己的自然生命;社会意义上,他们已经开始被清理出社会关系,而如果人确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们就已经部分地走向死亡了。
《疾病的隐喻》中,桑塔格认为疾病所承担的象征意义的重压使得患者蒙受羞辱,远比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还要致命。而如今,因为对患癌感到羞耻而“向癌症患者家属通报癌症诊断结果,但对患者本人讳莫如深”或是患者因为担心别人认为自己有“适合得癌症的性格”而不告诉亲友的情况似乎不像书中那么多了,但是绝症仍然会对病人的社会关系产生巨大的震荡。影片中,安妮特说,她的丈夫活得越久,就越少接到电话,得到访问。病人在朋友眼中已经提前成为死者,被认为难以正常地相处,被提前赶到一个封闭的只留下自我的孤独空间里,仿佛提早躺进棺材。这与对疾病的污名化的谣言是多少有关的,珍说,她的朋友见到她惊叹她看起来还不错,难道她得病了,就一定是躺在床上虚弱得起不来吗?人们不仅认为诊断书等于死刑通知,还将时间提前了,提早认为病人失去了一切精力,成为社交意义上的死人。而病人的陪护,也逐渐从社交网络中脱落:不仅没有人来寻访安迪,也不再有朋友来联系安妮特。陪护与患者被一同关在了封闭的盒子里,直到患者的社会关系会在葬礼举行的时候被重新唤醒,葬礼召集了所有故旧,作为仪式调节了群体的精神危机,避免死亡破坏社会的凝聚力,搅乱社会平衡。[4]
二、死的观众
影片中,治疗师说到:“绝症会残忍地破坏一段感情,没人能够明白面对死亡是什么样的滋味,即便是你的伴侣;将死之人也无法明白地目睹死亡。我们希望通过让绝症病人与其他身处相似境遇的人分享心境会使得他们能够重新处理好自己的关系或更加积极地面对人生。”
有他人评论说它不应如此拍摄:影片中的故事结构、情节安排有过于明显的斧凿痕迹,构成了生者对于濒死之人的某种无礼的凝视,让它不像是严肃的纪录片而像是疯狂的死亡真人秀,且本身对于死亡的议题并没有做出很思辨性的探讨,并没有提出有分量的结论。此评不假:可以发现,影片制作团队很可能有一致的观点倾向性,如:将将死之人聚在一起会有利于他们互相理解,培养友情,恢复因疾病而破坏的社会生活。他们甚至可能对出演人员做出过暗示性的干涉,尽管索尼娅说:“你们希望我说我交到了朋友,对吗?”的时候摄影师的回答是“No”;此外,他们隐隐约约地表达无论如何活下去都比尊严死更加可取,在强调参与者们认识彼此之后决定继续化疗时总是显得得意,让人联想英国安乐死本就是不合法的,BBC毕竟是受英国财政资助的公营媒体。
他们配备了姑息疗法的心理咨询专家。第一集中专家与患者之间存在直接的矛盾:“你们专业人员在那儿说,姑息疗法很好。但你和我们根本不一样。(But you are not sitting here, not in the position we’re in. I have the right to say let me finish it.)”专家独白说:“他们全都不信任姑息疗法能帮他们度过病痛。我希望他们能正视疾病,不需要安乐死……”
拍摄者与主演们之间可能存在同样的观念矛盾,并且最终拍摄者站在专家的角度在看这一切,而对于注重尊严的死者,拍摄者没有彻底达到一个相对主义的立场,他们难以从绝症病人内部的信仰和价值观入手,他们有自己的成见,有一定的客体化嫌疑。
而且既然如此,影片最后自己没有发表太多对死亡的总结性的观点、看法,就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毕竟死亡波及远远不止一人,但最终只有死者死去。观念完全可以属于自己,保留一些尊重。追求生命质量还是维持生命,如何度过最后的时间,像影片中这样选择各不相同方不反常——死亡的答案不是能盖棺定论的事。
本文为【文化与社会】课程作业
作者 金书桐
参考文献
[1] 富晓星、张有春.人类学视野中的临终关怀[J].社会科学,2007年9月20日,第118页。
[2] 赵旭东.互惠人类学再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7月25日,第110页。
[3] 任丑.死亡权:安乐死立法的价值基础[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02期,第118页。
[4]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第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