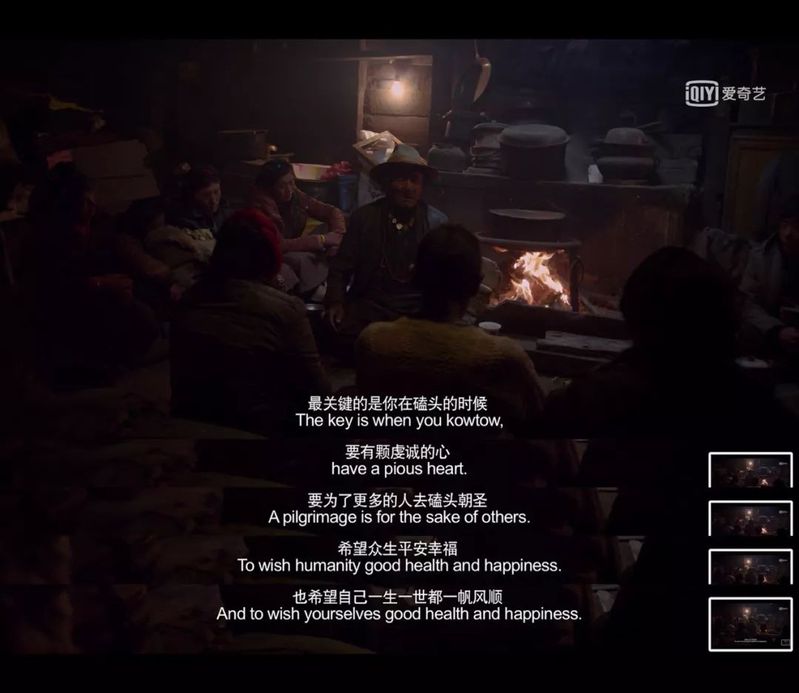《冈仁波齐》是一部以纪录片拍摄手法完成的剧情类电影,讲述了在西藏芒康一个藏族村落中,一行村民前去冈仁波齐朝圣的故事。片中朝圣的发起人叫尼玛扎堆,为了满足年迈的叔叔杨培在生前去见冈仁波齐的愿望,他决定带上叔叔去朝圣。嫁给了尼玛扎堆的三个儿子做妻子的斯朗卓嘎也决定带着九岁的女儿扎扎参加朝圣。斯朗卓嘎怀孕的姐姐次仁曲玛及其丈夫色巴江措也一起加入了朝圣的队伍。村中听闻尼玛扎堆一家要去朝圣的仁青晋美和仁青旺佳兄弟俩也参与了进来。临走在准备朝圣路上的物资时,前来帮忙的屠夫旺堆表示,自己杀生太多,罪孽很重,想要去朝圣来洗清自己的罪恶;同村中的姆曲家盖房子发生的事故导致两死两伤,姆曲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负债,他也想参加朝圣,为自己的心灵找到解脱。由此,由十个藏族村民以及一个尚在母亲怀中孕育着的小生命组成的朝圣队伍踏上了前往神山冈仁波齐的路。
这部电影的拍摄手法与被认为是人类学社会影象记录的“开山之作”——《北方的纳努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北方的纳努克》中,导演用“搬演”的方式展现了爱斯基摩人的日常生活(其隐瞒纳努克平时用猎枪狩猎的事实,刻意表现因纽特人的传统鱼叉狩猎法等拍摄手法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冈仁波齐》中,朝圣的十位藏民是导演在西藏芒康拉普村找到的素人,他们符合了导演在拍摄之前构思好的人物设定:一个很可能在朝圣路上死去的年迈老人,一个会在朝圣路上生产的孕妇,一个“罪孽深重”的屠夫,几个青壮年和一个孩子。因此导演实际上是本片中朝圣活动的发起人,他使用了纪录片的拍摄方式,以此最大限度地真实展现藏民“磕长头”的全过程。
一、观电影之内:走在朝圣路上
(一)神圣之域冈仁波齐
在西藏本土原始宗教苯教中,冈仁波齐山位居四大神山之首,是苯教的发源地。苯教是由西藏的原始萨满信仰演变而来的,是西藏历史上最早的宗教,其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日月、雷电冰雹、山石草兽等各种自然物以及自然界的神灵和鬼魂。冈仁波齐在苯教中被赋予了神圣的地位,它作为神(三一真神湿婆)的居住之所,是信徒们进行祷告、求神启示的静谧之地。传说围绕冈波仁山行走一圈(又称“转山”)能够令人俗人超脱,转10圈能在500次轮回中免受下地狱之苦。特别是在藏历马年时的转山一周,相当于平常年份转山13周。[1]
朝圣路上的出生:一种幸运
影片中的朝圣正是发生在藏历马年,朝圣队伍中的属马的色巴正是因为本命年的原因参加了朝圣,次仁曲玛也是为了即将在马年出生的孩子而去转山。在朝圣途中,次仁曲玛的孩子丁孜旦达出生了。同行的人都称他与神山有缘份,是个非常幸运的孩子,一出生就得到了神的祝福。对于藏族人民而言,他们以游牧为生的习性使得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非主宰者,在哈维兰的书中这种观念被称为自然主义世界观。[2]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宗教就变得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青藏高原的山地作为藏族人民生活空间中的一个基本空间因素,逐渐成为了人们的生活和宗教信仰的基础,其中如冈仁波齐这样有着特殊风貌的雪山便成为了藏民生活中的崇高存在,与重要的神祗相关联。由此可以看出,宗教中不只存在着对灵力(泛生论)与超自然生命(泛灵论)的信仰,也存在着对特定的地理环境(位置)的崇拜。
冈仁波齐峰下的死亡:一种福报
在朝圣者们到达冈仁波齐山脚下进行“转山”后的当晚,尼玛扎堆的叔叔杨培在睡梦中过世。第二天醒来的尼玛扎堆等人发现后,立即找来了喇嘛为他超度。在这过程中,一行人并没有哭泣,这也许与他们的信仰、自然主义世界观有关:人从自然来,终究要回到自然中,不必为肉体的逝去执着,哭喊反而会打扰逝者的灵魂,应让他的灵魂安静地找到归处。尼玛扎堆说,叔叔这一生为了照顾他还有家中另外的两个孩子,在妻子死后没有再娶,他一生没有与村子中的人有过口舌。在冈仁波齐峰下走了,是他与这神山的缘分,是他的福报。
最后,在喇嘛的唱经声中,白色哈达包裹的尸体放置在冈仁波齐峰下,等待着天空中盘旋的秃鹰来啄食,这是藏族常见丧葬仪式中的一种——天葬。虽然天葬仪式较为简单,但它与其他丧葬仪式一样,有着缓解生命逝去带来的危机感的作用。它作为丧葬仪式的一种,可以看作是一种强化仪式,用来允许活着的人表达对逝者的关切,排解自己与离世之人的情感上的维系。[3]在为杨培举行了天葬仪式后,一行人重振行装,收拾好心情又开始了“转山”之路。
(二)朝圣路上的“互惠”
在烈日当空下的“磕长头”,无疑是对人体力的巨大消耗。尼玛扎堆一行人在路边遇到了正在盖房子的藏族同胞,房屋主人亲切招呼地他们坐下喝茶。这在招待者看来,为朝圣者提供便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许因只是为做了这件好事,自己也能得到神的祝福。同样地,在尼玛扎堆等人在路边扎营休息时,看到一对兄妹俩人轮流拉着板车和毛驴走在朝圣的路上,也亲切地招呼他们过来坐下喝茶,甚至在自己余粮也不充足的情况下,分了一些糍粑给兄妹俩的毛驴。尼玛扎堆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在沿途中收到了藏族同胞的热情招待,自己也想将这种善意的行为传递给同样是朝圣的人们,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将这种善意与热情传递下去。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给予热情招待的房屋主人和尼玛扎堆赠与的糍粑,都算是一种一般性的互惠,他们并不期望自己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时刻得到对方的回报,仅仅是因为同为藏族同胞、同为朝圣者,有着互相帮助的义务;另一方面,在朝圣路上给予他人帮助就是用行动体现对神虔诚的心意,正如杨培每晚在帐篷里带领大家诵经时说的那样:“我们磕长头是为了众生的平安幸福,要把众生放在心里。”

图1 偶遇藏族长者的热情邀请
这种一般的互惠还在影片中别处有着体现。尼玛扎堆一行人用来运物资的拖拉机不幸在路上出了故障,一行人正准备就地扎营时,一位藏族长者正好经过。在了解事况后,他大方爽快地说:“到我家去住吧,我家很大。我的孩子也和你们一样去朝圣了。”于是一行人住到了长者家中,等待同伴去附近的镇上买零件修复拖拉机。在接受了长者酒肉的丰盛招待后的第二天,尼玛扎堆等人看到长者在修犁,便提出主动帮助长者犁地,有了几个青壮年劳动力的帮助,长者原本需要一个人犁的地很快就完成了。临别时,长者还送了一块羊皮子给刚生产完的次仁曲玛,以便她“磕长头”。可以看出,尼玛扎堆一行人与长者之间有着默契的“给予——回报”的互动,尽管彼此之前都是陌生人,正如德国学者图瓦恩说的,在给予、接受、回报这三个行动之间,两方建立起了互相帮扶的关系。正是由于藏族同胞(人类)有着这样的互惠原则,他们的朝圣路上并不会感到孤单和无助,反而拥有了更坚定的意志和前进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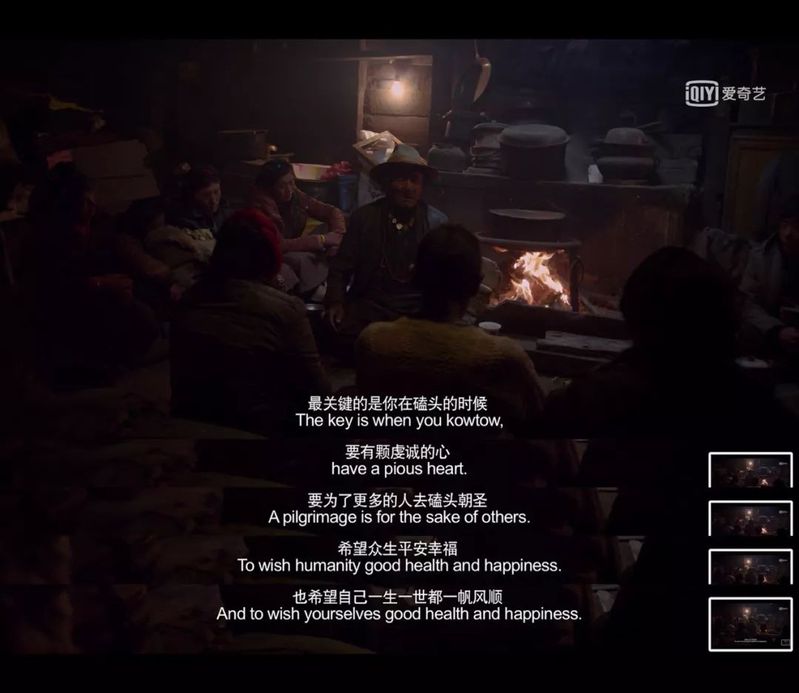
图2 长者对朝圣者们的叮嘱
一妻多夫是多偶婚中较少存在的婚姻制度,人类学家主要是在南亚的文化中对其有所描述:在喜马拉雅山脉,兄弟几个可能会娶一个妻子,以防止他们的财产(尤其是有限的土地)分成几份给他们的孩子;此外,如果其他兄弟必须在外面呆上很长一段时间,总会有一个丈夫在家陪伴妻子。[4]多个兄弟中,年长的那位被后代叫做爸爸。导演找到这十个素人藏民的村庄芒康,现在还保留有兄弟共妻的情况。影片中尼玛扎堆说,死去的叔叔杨培为了照顾孩子没有再娶,事实上杨培与尼玛扎堆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父子而不是叔侄。杨培的哥哥早年去世之后,杨培便以叔叔的名义承担了父亲的义务。同样地,在电影演出人物的介绍中,斯朗卓嘎也嫁给了尼玛扎堆家的三个儿子。在传统西藏社会中,兄弟共妻是人们为了应对生态环境的限制所采取的关系缔结策略。多夫一妻的大家庭避免了劳动力的流失与土地的分割,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兄弟之中还能有人外出务工,为家庭获得额外收益,另一方面,随着藏区的文明开化,年轻人的生计不再局限于有限的草场与耕地,兄弟共妻作为对当时生产环境的应对策略,也逐渐走向了衰落。文化相对主义由博厄斯提出,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与个性,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任何文化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不能用共同的、绝对的标准去衡量一种文化的价值。我们只有理解了某种文化所在的特定环境,才能有评判该种文化的资格。但这并不代表文化相对主义带来的效果都是积极的。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似乎在大体上都接受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熏陶,都知道除了“我们”文化之外,还有与我们平等的“他者”文化。而我们对“他者”文化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逐渐变为一种对“他者”的窥探。《北方的纳努克》虽然可以说是人类学记录片的开山之作,另一方面,它也迎合了人们对自己没有见过的人和事的好奇心,是一种对爱斯基摩人日常生活的刻奇。同样地,尽管《冈仁波齐》想展现的是藏民原始真实的朝圣旅途,但影片中的人物是素人扮演的,影片整体是有剧情的,电影情节是刻意制造的(尽管导演表示自己是在制造一种“不刻意”),这并不是一部真实的纪录片。这部电影在2015年上映时,一度成为当季票房黑马,原因在于,被定位为小成本文艺片的它将受众市场瞄准了创业投资圈和文艺高知,因为“磕长头”背后蕴含的精神修行题材似乎格外容易打动这类人群。作为观影群众的“我们”似乎把朝圣的藏族同胞当作了另外一个“物种”,带着猎奇的心态走进他们的世界,看到尼玛扎堆等人在“磕长头”路上的坚守会不由自主地感叹自己精神生活的空虚、缺乏信仰。换句话说,我们有消费他们信仰的嫌疑。相信绝大多数观影者并不信教,影片中路上出现的游客见到尼玛扎堆等人也只是投去好奇目光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下一秒这些照片就可能会出现在朋友圈里,并且很可能有这样的鸡汤配文:“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也许我们大多数人只学到了文化的相对性,却不能设身处地地去理解那份跪拜的虔诚,也无法感受到跪拜带来的无量幸福。 我们经常把许多事情是为理所当然。我们可能会认识到文化创造了一个包裹着我们的充满意义的世界,但在我们内心深处可能仍会认为,我们的动作行为和思想是自然的或者正确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我们民族中心主义的一部分,尽管有了这些认识,我们也很难从我们对世界的设想中自由地抽身。我在知乎、豆瓣影评上注意到,对于《冈仁波齐》这部电影中呈现的藏民朝圣行为,出现了很多反对与鄙夷的声音。人们不自觉地根据信仰的不同将自己与藏民区别开来,一边是以儒文化为核心的汉族信仰,一边是对强调精神修习的藏族信仰。反对的观念主要与西藏落后的经济面貌有关,即愚昧的宗教信仰阻碍了西藏生产力的发展。在影片中,尼玛扎堆等人用来运物资的拖拉机车身上,印着“扶贫开发”的字样,对此很多人质疑,国家对西藏地区扶贫投入的资源却被用在了不能提高生产力的宗教信仰上。

图3 拖拉机上的“扶贫开发”字样
对于藏民在公路上跪拜的行为,很多人也不尽赞同,因为时常有运送物资的卡车在蜿蜒险峻的山间公路行驶,一行人在没有防护栏的情况下与来往车辆很容易发生事故,时常有在国道318朝拜的藏民遭遇车祸。当年援藏队伍用辛劳和鲜血筑起的交通生命线如今还只是被当作通往神山的通途,让藏民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图4 蜿蜒曲折的国道318
还在上小学的扎扎为朝圣耽搁了一年的学业。在朝圣路上,当姆曲问身体不适的她还能不能坚持走,要不要休息一下时,扎扎妈妈说:让她磕,磕头长见识,磕头很好的。”对现在中国社会中大多数家长而言,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获得一定的文化资本,从而在教育竞争体系中脱颖而出,成为对家庭、对社会作出生产力贡献的人。而对扎扎妈妈这样有着宗教信仰的藏民来说,“磕头”就是一种与神沟通、获得神启的方式。这种举动让很多接受过现代高等文明教育的中国人很难接受,他们认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宗教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所谓的朝圣只不过是用体力上的付出逃避世俗痛苦,将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于神,却无法改变家庭贫穷落后的现状。而像扎扎这样尚未有自主意识的儿童,被动地接受了这种宗教信仰,失去了规划自己精神生活的自由,相比之下,作为汉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实用的生活方式,而未对人的生活的终极目标作出规定。在这种生活方式的引导下,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经济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个人能够在践行这种生活方式的同时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挑选自己最适合的精神信仰和实践,而不一定是对宗教的信仰。

图5 扎扎妈妈对磕头的认识
在藏族的宗教信仰与汉族对儒家文化的信仰之间分高下,这种做法在我看来并不妥当。对朝拜的信仰真的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愚昧吗?能发展生产力的信仰才是好信仰吗?在社会进化论者看来,超自然信仰最终都会让位给科学,文明最终是进步的表现。如霍布斯认为,宗教信仰是基于无知和非理性的想法,我们应该根据事实提供的证据来推翻信仰,摆脱自己的无知,拥抱“真理”,以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理性推翻信仰。但就像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真理是否是“真实“那样,我们又怎么能从藏民的角度出发,断定朝圣、转山带来的神的祝福、获得的无良幸福是虚假的?现代文明中对学科的研究都是建立在“真理是真实的”这一基础上,如果真理不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所建构的学科大厦将会轰然倒塌。同样地,朝圣者将朝圣能带来福报作为信仰,从他们的认知角度出发,信仰神、朝拜神是有逻辑的、合理的行为。如果我们坚守着有信仰高低之分的观点,正如哈福德所说,我们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民族中心主义:“我知道的我了解,你知道的只是你相信——知道和我的知识发生冲突的程度。”[5]也许就像卢克·拉斯特在在《人类学的邀请》中所写的那样,宗教或许是最容易产生根深蒂固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地方,当我们用民族志的“本地人观点”去理解另一个信仰系统的空间时,存在与信仰之间的等级就会开始消散,而我们所有不同的信仰,或许都来自同一种被我们感知的东西。[6]另一方面,很多人对于朝拜信仰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一点耿耿于怀,用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去衡量当地藏民的生产力水平,并且希望他们能向我们看齐,这也可以看出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子——只有发展到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才是最恰当的。我们不必捍卫任何民族参与任何文化实践的权利而不管他们具有什么破坏性,但是信仰对于生产力的阻碍远没有非洲割礼、16世纪的阿兹特克人人祭那么极端,况且“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否就一定能够带来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一问题还有待商榷(觅食社会生产力较农业社会低,但人们也能自给自足且不用异常辛苦地劳作[7])。人类学家通常以每一种文化自身的方式去考察每一种文化,辨别文化是否满足人们的物质的、社会的、心理的需要,以此作出明智的判断。[8]有人类学家总结出了衡量是否满足需要的指标,大致有:人群的营养状态、总体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暴力、犯罪和违法行为的发生率;人口结构及其稳定性,家庭生活的安宁;以及群体与其资源基础的关系。[9]如果某种特定的文化能够满足特定人群的这些需要,我们便无需用带着有偏见的目光去评判他者文化。正如片中藏族长者说的那样,过去的耕地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活动,更是一种庆祝天的馈赠的仪式。耕地时还要带上酒肉载歌载舞,并不在意一天要完成多少耕地任务。他们对这种生产方式自得其乐,我们又何必催促他们赶上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呢?也许用庄子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一句话便能总结吧。

图6 长者回忆年轻时的犁地场景
纵观《冈仁波齐》全片内外,我想说的是,无论导演是以一种刻奇的、还是消费信仰的心态完成影片的拍摄,也不论藏族宗教信仰在这其中的优劣,这部影片将藏族朝拜者的信仰与文化展现在观众面前。在这条朝圣路上,有人出生了,有人死去了,都是人生常态,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只不过是族别、文化、信仰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既然不可消除,我们也不必带着偏见去评判,做好一个合格的看客就已经足够。我很同意在某位网友在豆瓣上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以此作结:“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得闪烁着思辨的火花才值得一看,我蹲在河边看一块石头上的花纹,不是因为我能够从中得窥这世界的奥义,是因为我想了解它。”复旦社会学 朱茜齐
[1]维基百科:冈仁波齐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冈仁波齐峰
[2]《文化人类学:人类的挑战》,(美)哈维兰等著;陈相超,冯然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P305.
[3]《文化人类学:人类的挑战》,(美)哈维兰等著;陈相超,冯然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P319.
[4] Nancy Levine, 1988, TheDynamics of Polyandry: Kinship,Domesticity, and Population on the Tibetan Border,Chicago: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5] Hufford, David J. 2007,“Traditions of Disbelief.” New YorkQuarterly 8: 47-55.
[6]《人类学的邀请》,(美)卢克·拉斯特著;王媛,徐默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P204.
[7] Jared Diamond. 1987. The WorstMistak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Race.Discover.
[8]《文化人类学:人类的挑战》,(美)哈维兰等著;陈相超,冯然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P41.
[9] Fox,R. 1968. Encounter with anthropology.NewYork: Dell. P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