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言学者认为,方言是语言的变体,同属一种语言的方言有共同的历史来源,词汇和语法结构[1]。宁波方言和上海话,苏南方言和其他浙北方言同属于吴语区的太湖片区,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吴语的核心区域。[2]据历史记载,浙江地区从秦代开始的政区沿革就十分稳定,省内的方言一致性很高。宁波话尤其如此,现有的几个县(区)基本是从秦代三个县析置而来,所以方言的沿革比较稳定,市内的方言一致性很高[3]。
宁波话面临的问题
作为一个吴语地区长大的人,大学拥有三个广东室友的好处之一就是用方言和家里人打电话的时候可以充分保护自己的隐私。用方言和家里人打电话一直是我的习惯,实际上,就我了解而言,大多数宁波人在家庭内部的交流中都倾向于使用宁波方言,在朋友的聚会中倾向于多使用一些,于此泾渭分明的是工作或者公众场合中,即使在场的都能够流利地使用宁波话,人们也倾向于使用更为正式的普通话来代替,人们默认只有在小圈子里使用方言。
我的宁波话已经算得上三脚猫,但还是可以傲视一下我的高中同学,他们中不乏对此一窍不通的本地人,上个月就有一位向我求助,她要在舞台剧里扮演一个叨叨的上海女人,因为现代的上海话有很大部分和宁波话相近,于是就想到了找我。宁波方言在年轻一代中的掌握情况并不乐观,其中不乏我这样口音并不标准的使用者。
宁波话与现代文化
宁波话在年轻一代中的尴尬境遇首先在于教育的缺失。实际上,宁波话的书面教材并不罕见,来华传教士和当地学者都有整理过相关的手册,但是这些书面教材应用很少,宁波话的主要传承方式还是家庭内部的口耳相传。我在高中时候的语文老师是目前为止我所知的唯一一位讲宁波话引入过语文课堂的人,他曾经借着宁波话讲解过文言文,也曾经试着让我们用方言朗诵一首古诗。但是归根结底,有着主动将方言引入课堂的意识的教师很少,更不用说主动引导学生去了解其中文化内涵的。所以家庭教育才是宁波话学习的主要来源。
然而,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父母的家庭教育有意识地向着普通话倾斜,加上城市的现代化,让市区内长大的儿童大多一出生就处在被普通话包围的环境中。并且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通常更加正式和疏离,并不像乡村那样有着明显的差序格局,所以年轻人学习更加正式,现代化的普通话的动机会比普通话更加强烈。
此外,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亲族聚居的模式在逐渐消弭。家庭中熟练掌握方言的老一辈和年轻人通常不住在一起,这种地域上的隔阂也限制了年轻一代的学习来源。更不用说老人们也渐渐会说一口普通话了。
其次,年轻人们对宁波方言的抵触有可能是对其承载一部分的“老宁波”文化的抵触。按照Sapir-Whorf的假设,语言塑造了使用者的世界观,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形成,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宁波话原先在田间乡下使用,尾音常常是去声,显得有力,这种“石骨铁硬”的特点甚至衍生了一句俗话“宁和苏州人吵架,也不和宁波人讲话”。在传统的审美中,宁波话就不符合人们对吴侬软语的幻想,而在现代的审美来看,宁波方言中大量的乡土的内容也显得过时。其中有不少俗语和童谣,虽然音律和谐有趣,但是因为内容过于粗野直白,有类似“面孔红咚咚,每日忖老绒(老婆)”者,自然很少出现在现代人的育儿清单里。加上对标准的普通话的追求,带有方言的口音自然被贴上需要矫正的标签,连带着方言就被认为是“乡土”的,低学历的表现,人们想要的是更现代化,更“文明”的内容——原先传唱街头的宁波老话自然被扫到“糟粕”的灰尘堆里去了,连博物馆都是进不了的,更遑论复兴了。

宁波话与外来人口
人口的变迁一向是语言演化的重要原因,外来人口的一些特征,例如数量,迁徙距离的远近,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关系都会对方言产生不同的结果[1]。宁波作为长三角地区的发达城市,吸引的主要是周边城市的打工者,也有一部分投资者。
与古时候的移民不同的是,外来打工者的方言对于本地的方言影响较小,首先是因为打工群体来自五湖四海,在居住环境上很少有聚居的。其次是普通话作为一个媒介,削弱了外地人融入本市所需要的语言学习的动机,普通话在公共场合的广泛使用减少了使用不同语言的沟通成本,但是也有例外,我知道有一些台州三门县的打工者为了省钱,会在宁波周边的郊区中租房子住,时间一长会形成一个小团体。加上本地人往往向城市中流动,在一些村落和城乡结合部,同乡的打工者有可能占很大一部分,他们之间互相交流会用台州方言,但是和本地居民交流依然用普通话或者宁波话。在这种混居的村落中,本地村民对于外来打工者往往有一种优越感,而且客观经济条件通常更加优越,外来打工者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环境,有时也会学习宁波话。
有趣的是,近年来比较有影响力的一本宁波话教材《贾军教你学说宁波话》(贾军是一位在当地有影响力的方言新闻节目主持人)也被定性为是“供初到宁波工作以及来宁波出差 、旅游的外省 、市人使用”,外来人口为了方便交流和融入这个城市会有一定的动机去学习宁波话,无论是学习的动机还是对标准化的追求上,外来人口都比本地的年轻人更有热情和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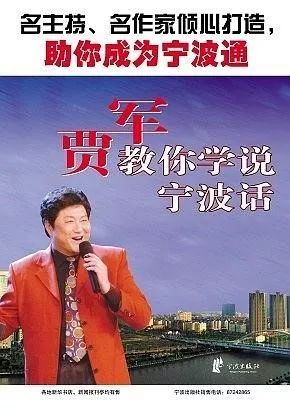
总体而言,外来打工者对方言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普通话的使用产生的。人口的机械增长会使城市的文化更加多元,而普通话则通行于大多数居民之中,为了交流的方便,和一个陌生人打招呼时用普通话看起来更加明智。
但是不可否认,外来文化的涌入也会唤起本地人寻求身份认同的迫切性,使用本地方言有时候看起来是一种“高贵”的标志,现在本地媒体报道宁波话,都力求原汁原味和纯正标准,其实也反映了居民寻求文化根源和身份认同的心理。
宁波“新”话
以宁波话为载体的甬剧算是宁波方言里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早些时候也叫宁波滩簧,年轻一代中爱好者不多,在老一辈中也不是人人都听,我的长辈就更喜欢听越剧。如果说要把宁波话的音律美表现出来,我以为是没有比甬剧更合适的了,只是也许剧目内容实在不符合年轻人口味,眼下也日渐衰落。目前专业表演团体就只有一家。
倒是宁波市的地方电视台有新招,他们近年也在播放一些使用方言的新闻类节目,其中以《来发讲嗦西》和《讲大道》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后者已经推出了自制剧,当然也是以宁波话为语言,通过媒体的形式挽救方言,是一种不错的手段。本市的年轻人虽然较少看电视,但是对于陪着爷爷奶奶这种节目还接受良好,加上这些电视节目时常会报道一些宁波的传统文化和手艺,还有一些宁波老话的竞答环节,对于传承宁波智慧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年轻人对于传统方言也不是一味的被动,互联网作为年轻一代的阵地,其中也能看到方言被书面化的情境,特别是在强关系网络的社交媒体中,用户同质性高,同乡之间更能够一下子理解其中的含义,获得更强的身份认同和交互作用。例如就有人用方言为一些知名的电视段落重新配音,搞笑之余也唤起了人们对方言的认同,还有将“秋裤”的方言用“me more cool”的形式表现出来,语音相近,令人会心一笑。这种基于方言形成的身份认同与传播范围广,效率高的互联网结合,更能吸引本市居民的注意力。
宁波话的现状总体而讲并不乐观,对于方言的学习还处在被动的,潜移默化的阶段,对于其中的文化意义并没有多大的体会和学习的机会,但是一旦自我的身份标志被强化了,比如周围的外来人口增加,人们就会更有意识地去强化自己的这种身份认同。同时,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人们也会越来越重视对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而一个没有自己语言的城市是没有自己的文化的,宁波的相关部门也会更加重视本地方言,将其作为一种标志,深挖其中的文化含义,促进方言教育,从而塑造起本地人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讲,由于语言本身是变化的,外来的文化产品其实也能够通过改编,再创造成为方言的载体,互联网的出现为地方方言和主流文化之间搭起了桥梁,也为年轻一代和传统方言搭起了桥梁。如何用方言创造符合年轻人口味的文化内容,使宁波老话重新焕发活力,将会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周振鹤, & 游汝杰. (2006). 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p13
[2]周振鹤, & 游汝杰. (2006). 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p87
[3周振鹤, & 游汝杰. (2006). 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p59
复旦社会学 夏林璇
复旦人类学 赵雅卓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