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基于对纪录片《月事革命》中体现的月经禁忌和女性生存状况现象的分析,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从污染、仪式、禁忌等角度入手,对中外月经人类学既往研究进行简要综述,研究月经现象及其附着的一系列惯习中体现的性别分工视角,且提出可能的在当代打破月经禁忌成见的方式。
关键词:月经 文化人类学 性别 禁忌污染 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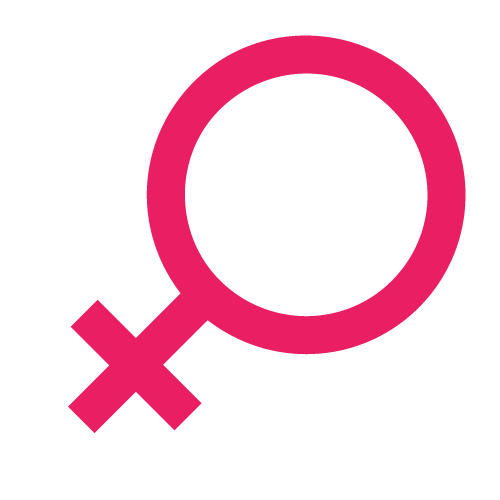
“我想要做一名警察,”皮肤黝黑、五官深邃的Sneha坚定地看向镜头,“我想把自己从婚姻中拯救出去。”
2019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月事革命(Period. End of the Sentence)》中女性是核心议题, “飞翔”卫生巾则是这个仅25分钟的影片的叙事线索。故事起源于加利福尼亚的学生团队发起的“致力于帮助欠发达地区因月经而失学的女性The Pad Project”运动[1]。团队在印度哈普尔的凯蒂基拉村资助男子Muruganantham发明了卫生巾制造机。机器本身非常简陋,但对于周边村子的女性的生活却产生了意外的显著影响。在剖析这部影片的过程中,文化人类学有关于污染、禁忌的观点十分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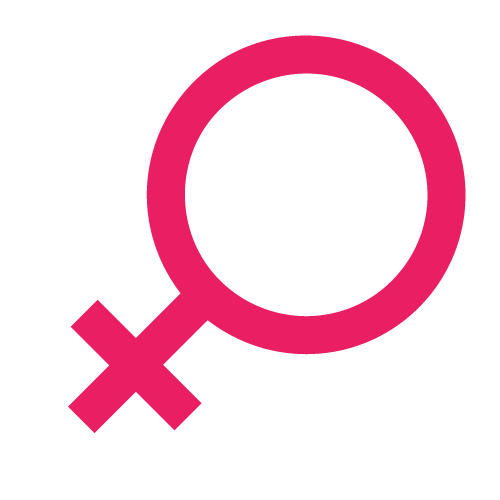
故事主线
《月事革命》采用顺叙逻辑。一开头,执镜者询问的 “月经是什么”的问题羞红了年轻姑娘的脸颊,穿着校服的女学生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年长的女性则气定神闲带着神谕一般的口吻解释着:流出的是坏血,只有神知道。男性呢?镜头前头发鬈曲的他们三两个结群在一起,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也一下噤了声。“是一种病吗?”,一个年龄较小的男孩探寻地问着,旁边的少年眼神里则露出会意的微笑。

图1. 男人的话,来自电影《月事革命》
月经对凯蒂基拉村姑娘的影响,不止是羞于启齿这么简单。这个带有禁忌意味的概念为女性的生活塑造了许多有形的边界。首先,月经期的女性被认为是“不干净的”,不被允许进入寺庙。建构这一话语的途径在于女性的经血会污染圣殿,从而激怒神灵,神会不愿意倾听人的祈祷。其次,鉴于卫生巾在此地尚未普及,经期的女性依照传统贴身使用废弃的布条吸收经血。对于还在上学的姑娘来说,更换布条需要去很远的地方来躲开男性的目光,更换下来的布条还有可能被野狗叼走扔在路中间造成困扰。纪录片里,一个女孩就因为月经不得不放弃读书,尚处花季的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再次,村里的女孩常常因为“肮脏”的经期受到嘲笑与讥讽,她们没有什么自由,许多人早早嫁人,也不被鼓励出去工作。
影片从几个“逆反者”的出现开始转折。第一个角色便是文章开头那位干练的姑娘Sneha,她身形瘦长,有一种凌厉的英气。怀着一颗警察梦的Sneha和整个村子的男权传统对抗。她反对村子里要求经期女性远离寺庙的要求,“我们祈祷的神也是女性,她应该能够理解我们。”看着村子里的女性,Sneha流露出一种无奈又坚定的神色,她之所以梦想成为警察,一方面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村子里更多的女性觉醒起来。第二位“逆反者”是Shabana,她很“前卫”地在村子里给女孩们开性教育课,还向她们展示卫生巾的用法。老太太精神劲头很好,讲课时自信的神态非常动人。第三位“逆反者”就是受“The Pad Project”资助设计月经制造机的Muruganantham[2]。他希望自己设计出的机器可以在村子里实现卫生巾的普及(目前普及率还不到10%)。
在“The Pad Project”的支持下,三位逆反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创业运动”。他们把自己的产品命名为“飞翔”。Muruganantham在上游生产、包装卫生巾,Sneha和Shabana则挨家挨户地向女孩们普及、推销产品。开始并不是特别顺利,但渐渐的,有女孩勇敢地买下了第一包,于是第二包、第三包也成功卖出,越来越多的姑娘拥有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包卫生巾。Sneha和Shabana看着一天之内收回的180卢比(约2.59美元),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图2. 女孩们学习制作卫生巾,来自电影《月事革命》
更革命性的情节发展在于女孩们选择从消费者化身生产者加入三人的队伍,她们把卫生巾生产机器叫“好奇机器”“之前都是男人赚钱,现在我们也可以赚钱给男人了。”于是“飞翔”的活计越做越大。这里导演的镜头安排很耐人寻味,宏大的构图和恢弘的配乐在狭小逼仄的工作间交汇,卫生巾的生产顿时有了一种使命感。“女性是任何社会的基础,神创造的世界上最坚强的生物,不是狮子,不是大象,而是女性。”导演借影片中的男
子之口说出了这句话,极具女性主义色彩。
影片结束于Sneha。她拿着从卫生巾机器上赚来的钱支付报考德里警察的培训费。“我会赚很多钱,实现父母的愿望,也实现我自己的愿望。”在昏暗的灯光下,Sneha憧憬的笑容和泪光一样动人,“等我去了德里,我会去每家店找‘飞翔’卫生巾”。她哽咽了,镜头切换到了外景,黑夜里传来了一阵摩托车的轰鸣。接着影片戛然而止。

图3. Sneha的决心,来自电影《月事革命》
月经作为仪式性的不洁与禁忌
(一)被神秘化的月经
张爱玲(2007)在《谈女人》中曾形容:“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则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这大抵与影片中Sneha说的“神也是女性”表达的是一个意思。但就是这样富有神性的、充满温情意味的女性,却因月经这一生理机制而在人们的观念中成为污染源。《圣经·旧约》的《利未记15》这样记载:“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洁净;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若有其他物件,一人摸了,也必不洁净到晚上。”(Bible Gateway,2011)月经,乃至于月经期的女性,都被看作是不洁、失序的象征。
经期的女性常常被采取某种隔离的政策与其他成员区分开,譬如影片中女性被禁足神坛,亦或是如澳大利亚金伯利地区的女性在经期的时候与男性隔离,阿拉佩什人和夏威夷人专门为经期女性准备“月经小屋”等习俗(金泽,2002:341-342),都反映了人类对于这种周期性的、制度化的、专属于女性的、从身体向外流血行为的特殊情感。人类学不乏对于月经的研究,二战以前,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落足于部落社会的月经传统上,二战后则转向对于与月经相关的文化现象的解释,甚至出现了“月经人类学”这一领域(张小红,2014)。相较之下,国内的月经人类学研究起步晚,体量少。民俗学者江绍原被认为是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开拓者,在最初成果《中国人的天癸观的几方面》中,江绍原提到中国人对于月经的看法呈现明显的分异:一部分人把它看作与疾病、死亡平齐的污秽之物,另一部分人则将其供为圣物,认为经血可以解毒治病(江绍原,1926;李金莲,2012)。李金莲教授在月经领域做了丰富的宗教人类学研究,她认为对月经的禁忌可能就起源于先民把牵涉到流血的行为看作是“圣礼”的倾向(李金莲,2006:155)。“神圣”与“污秽”看似是两个极端反向的概念,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的边界非常模糊。“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先民的信仰之一,比如道格拉斯(2018:15)在《仪式性的不洁》中介绍的哈维克妇女用神兽母牛的粪便掺水去清洗污垢的行为,“污染”在工具性和表达性的层次上都发生着作用。这一系列的研究都致力于把人的身体从原本纯粹动物性的生理科学领域剥离开来,更多地去研究其文化意涵。正如巴里(2000)所说,身体无疑是一种社会现象。
对于“污染”概念的讨论尤其富于文化人类学意味。玛丽·道格拉斯认为污染的法则与道德法则存在联系,确定不洁本身起了排斥和构建边界的作用(道格拉斯,2018:xxii)。污垢是一种“无序”的表现,是“东西放错了地方”(道格拉斯,2018:14)。“经血”则是厌恶与恐惧的凝结,这种厌恶天然地带有一种否定自然的意味,因为“我们来自于污物”(巴塔耶,2003:48),它时刻提醒着人们己身与自然不可分割的关系。对于经血的焦虑映照着人们对于自己出生的思考与恐惧。
因此,月经在很多文化承担一种神秘化的任务,月经期的女人也被看做神秘的(李金莲,2006)。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中,月经的故事都占据有一席之地。神秘的事物往往伴随着危险与不确定性,存在破坏现有秩序的倾向,当人们的理智被恐惧钳制,禁忌与污名化便成了积极应对危险、重组环境的工具。
(二)月经作为仪式与禁忌
无论是基于影片叙事的方式,还是女性日常的经验,月经的内涵绝不仅仅限于一种生理现象,而无疑是一种伴随着禁忌的仪式性行为。道格拉斯(2018:45)在《洁净与危险》中提到了部落社会丰富的涉及月经、生产和死亡的仪式。江绍原(1926)也提到中国古代社会五种经期妇女禁止进入的场合:“蚕室、腌冬腌菜或做酱、折或烧纸钱、泡豆芽菜、小儿出痘疹。”《月食革命》中,女孩们对于月经这个单词的羞于启齿,女性被禁止接近神庙,男性对月经的陌生,以及村民们将卫生巾生产机器称为“好奇机器”等等行为,都反映了月经的禁忌性特质。
经期中的女性会受到一系列身体规训,比如中国的父母会教育女儿不可以喝冷水、不可以吃刺激性的食物、不可以喝茶,甚至不可以高声唱歌、不可以捶背等,她们常常被认为是“虚弱的、生病的”。直到19世纪,女性月经的过程一直被医学界视为一种“病理化”的表现(Martin,2001)。使用卫生用品时,女性也被要求尽可能“隐藏”自己来潮的事实(Ginsburg,1996)。“月经成疾”现象中文化建构的力量不可小觑。
月经作为一种仪式和禁忌,有形无形中都在强化一种性别分工的模式。19世纪的生物学家Patrick Geddes(1890)在细胞机制的层面,以“同化作用(Anabolism)”“异化作用(Katabolism)”强辩所谓男性女性在生理上“根本性”的差异,并由此指出女性总是“被动的、保守的、怠惰的、稳定的”,而男性往往是“主动的、活力的、有追求的、多变的、热情的”(Geddes,1890;Martin, 2001)。这样的性别区分思想对于人类影响之深远不可估量,影片里哈普尔女性大多没有外出工作、经济独立的想法,十多岁就结婚生子,生活围绕着拓展家庭展开,被文化剥夺了选择命运的权力。因此,挑战传统形成鲜明反差的Sneba、Muruganantham才显得那么令人尊敬,但反思观众这种“觉得抗争的女性可贵而难得”的心理,其实也反映出当代人的思想已然接受了性别分工思想的规训。

图4. 校长的话,来自电影《月事革命》
月经禁忌影响了人们的话语。“月经”“卫生巾”这些简单的词语,在影片中成为女学生长久的双颊绯红与吞吐不定;卫生巾被称为“好奇机器”。其实影片外的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月经”其词在中国日常语境下甚少出现,女孩们会用“姨妈”代指这一生理现象,回避耻感的同时也增添一抹亲昵意味。人学习说话的过程,就是一种学习调节言语行为的具体语码的过程,他学到的是他所处的社会结构对他的要求(Bernstein,1964)。语言承接了呈现社会结构的使命,也建构着我们看到的真实世界。在一遍一遍隐没禁忌话语的行为中,人们强化着性别权力世界的统治逻辑。
(三)女性卫生产品对主体价值认知的塑造
“飞翔”牌卫生巾是影片的主线,围绕“飞翔”展开的是凯蒂基拉村的女性——以及一些男性——争取女性话语权的故事。相对于布条,卫生巾给予了女性更方便的处理经血的方式,更加卫生清洁,降低了患妇科疾病的风险,也给予女性在经期工作与学习的机会(原本经期女性只能裹着脏布坐在家里);其次,使用一次性的、干净、洁净的卫生巾,与从前随手拿来的、不清洁的脏布、树叶、土灰相比,作为一种后天建构的惯习也在不断塑造着女性认同自我价值的过程。布迪厄认为,惯习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会内化为人们的意识,去指挥和调动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成为人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模式、行为策略等行动和精神的强有力的生成机制(宫留记,2007)。回顾历史,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卫生产品的进步对于打破传统性别分工偏见与争取女性自主权意义重大。女性卫生用品挑战着传统的男权统治逻辑(Ginsburg, 1996)。参照Mary Douglas 和 Isherwood (1979)的说法,“The essential function of consumption is its capacity to make sense”(1979:62),当《月事革命》中害羞的小女孩买下第一盒“飞翔”,女性自我认同的心态便悄然开始转变,看似坚不可摧的男权统治逻辑裂开了一个口子。
结语:对于挑战月经禁忌的一些思考
一直以来,学界不乏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妇女使用经期卫生用品偏好的研究。低收入国家针对学龄女性的月经卫生管理(MHM)是长期被忽视的工作(Sommer and Sahin,2013),Mason等人(2015)在西肯尼亚的30所学校针对初中女生对于经期卫生用品的接受度展开了质性研究,他们发现,肯尼亚女孩们使用卫生巾、月经杯的初期会感到恐惧,但是习惯之后,女孩们表示自己为“不会再有经血漏出与奇怪的气味”而感到“安全”,不用时刻为担心别人嘲笑自己而提心吊胆,可以像往常一样按时上学而不用因此辍学或耽误课程。Phillips-Howard等人(2016)对MHM的综合评估结果也显示,过往的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女性普及卫生用品的使用方法的努力,对于改善当地妇女经期卫生状况有积极意义。

图5. 经期产品Flex Disc投放在Youtube的广告
此外,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更多女性用品的广告。比如Youtube上最近投放的Flex Disc,就是一款比较新型的女性用品,它最大的优点在于允许女性在经期无障碍地进行性生活。我是在浏览一个与此产品毫无关系的视频时看到这则广告的,广告视频中的女性大方自信地对产品的功能特点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讲解,她说“I love sex so I am in love with Flex Disc”。乐观点来看,打破话语禁忌本身就是改变的第一步,我们这一代相对于上一辈人更少地被月经约束,或许彼时Ginsburg(1996)描绘的女性对于经期需要藏藏掖掖的时代正在慢慢退潮,人们,尤其是女性自己,对于古老的月经禁忌也在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与解构。

图6. 经期产品Flex Disc官网广告
复旦社会学 张曼宁 推介
复旦人类学 赵雅卓 编辑
参考文献:
[1] The Pad Project官方网站:https://www.theThe Pad Project.org/,网站接受捐赠。
[2] 事实上,Muruganantham的故事在2016年就被拍成电影《护垫侠》(Padman),但《月事革命》突出强调的是女性主体在这场卫生巾运动中的地位,展现了一种不同的视角。
[2]宫留记,2007,《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3]金泽,《宗教禁忌》,200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江绍原,1926,《中国人的天癸观的几方面(一)》,《晨报副刊》第3期。
——,1926,《中国人的天癸观的几方面(续)》,《晨报副刊》第13期。
[5]凯瑟琳·巴里、晓征,2000,《被奴役的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6]李金莲,2006,《女性、污秽与象征:宗教人类学视野中的月经禁忌》,《宗教学研究》第3期。
[7]李金莲、朱和双,2012,《中国现代民俗学者的月经禁忌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
[8]乔治·巴塔耶,2003,《色情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9]谢国先,2001,《走出伊甸园——性与民俗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0]张爱玲,2007,《色,戒》,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1]张小红,2014,《污染力与女性:人类学视角下的月经禁忌——基于闽南山河村的考察》, 《昌吉学院学报》第2期。
[12]利未记 15. (2011). Retrieved May 1, 2019, from : Bible Gateway: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88%A9%E6%9C%AA%E8%AE%B0+15&version=CUVMPS;BDG
[13]Bernstein, Basil 1964,“Elaborated and restricted codes: Their social origins and some consequenc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6.
[14]Douglas,Mary & Isherwood, Baron 1979,The World of Goods: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New York:Basic Books.
[15]Ginsburg,R. 1996,“ ‘Don’t Tell, Dear’: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ampons and Napkins.”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1.
[16]Martin,Emily 2001,The woman in the body: 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production,Boston:Beacon Press.
[17]Geddes,Patrick & J.Arthur Thompson 1890,The evolution of sex,New York:Scribner and Welford.
[18]Mason, Linda et al. 2015,“Adolescent schoolgirls' experiences of menstrual cups and pads in rural western Kenya: a qualitative study.” Waterlines 34.
[19]Phillips-Howard,P. A.,Caruso, B.,Torondel, B.,Zulaika, G.,Sahin, M.,& Sommer,M. 2016,“Menstrual hygiene management among adolescent schoolgirl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research priorities. ”Global Health Action 9.
[20]Sommer,M. & Sahin,M. 2013,“Overcoming the taboo: advancing the global agenda for menstrual hygiene management for schoolgirl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