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约八岁时于晋南乡村参加了一场葬礼。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葬礼,时虽未脱孩童懵懂,却对经历过的许多画面印象深刻。亲人逝去固大悲矣,然而何时流泪,何时哭悼,却不能完全按照个人的心意。一项接连一项的仪典,一个接连一个的来客,白色的布块在视线里交织往复,一天过后,伤悲未尽,劳累繁生,夜凉人散,涕泪已干。隐约中,我感到这种葬礼是不同寻常的——在这个过程中,悼亡不仅仅是几个近亲故友的事情,还涉及到了全村形形色色的人,甚至涉及到了与逝者生前无丝毫牵连的陌生人。葬礼绝不仅仅是为了让逝者亲故表达个人的悲痛,而在众人的注视下有着某些社会意义。

葬礼,在人类学的视角下是一种特殊的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范热内普,2012)。它标志着一个人从生走向死的过程,标志着一个人生命最终的完成。许多中国人都笃信“入土为安”——若尸骨没有被埋葬,亡者的灵魂必会漂泊不安。这反映了长久以来中国民间大众对生命、对死亡的看法:生命并不是结束于人生理死亡的那一刻;人的躯体和灵魂是可以二分的,人死后,躯体归于泥土,而灵魂则进入阴间(郭于华,1992)。因此,在传统观念中,人的死亡意味着人的灵魂从现实世界的躯体中脱离、走向阴曹地府的另一个世界。然而,这一重要的过渡仪式却无法由本人来完成。于是,责任落在了亡者的亲属上,他们要把亡者的躯体顺利地埋入泥土、帮助亡者的魂灵顺利地进入另一个世界。据考察,近现代北方农村地区较为通行的丧葬礼仪一般包含如下的程序:一,入殓,为亡者穿戴寿服,移尸入棺;二,告丧,亡者家人向亲属、邻里传报死讯;三,开吊,亲友前来吊唁,亡者家人设宴款待;四,出殡,殡仪队伍移棺送灵,沿路哭号;五,下葬,棺柩到达墓地后,孝子孝孙填土掩埋,焚烧纸钱,叩头举哀(郭于华,1992)。如是的一套程序完成,再加上日后按时的祭拜和供奉,亡者才算是“入土为安”,圆满完成了从阳间到阴间的状态转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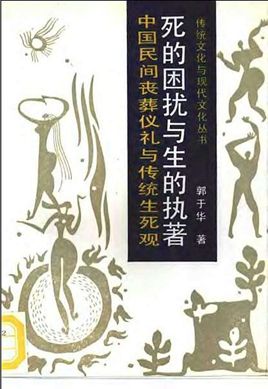
葬礼中,亡者的过渡仪式需要生者来执行。葬礼的程序虽然都围绕亡者这一核心展开,但是这些仪式不仅对于亡者有意义,对于生者来说也有着现实的意义。一个人的死亡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件,也是家族的事件、社会的事件,因为这意味着家族结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位置出现空缺。而这一空缺意味着其他位置间的社会关系将会发生改变。如果去世的人是原先的一家之长,那么在葬礼中那个组织丧宴、率领吊唁、走在殡仪队伍最前方的中心的人,往往就是众人公认的新的接替者。如果去世者不属于在家中地位显赫的人物,那么葬礼则是明确其身份地位的时机(李曦淼,2012)。亲属、邻里、村民等人是否来参与葬礼,体现了他们对于这一家族的声望与地位的看法。于是,葬礼得以实现的规模、形式不仅与亡者在家庭内的地位有关,也与亡者家庭在村庄里的社会地位有关。葬礼无声无息地完成了一次社会秩序的梳理。

因此,葬礼的公共性为葬礼上的行为表现赋予了丰富的社会性内涵。哭泣是一个几乎贯穿葬礼始终的行为。尽管对于个人来说哭泣是一件自主的事情,但是葬礼处于众人目光的注视之下,什么时候应哭号悼念,什么时候应克制情绪,葬礼的模样回答着社会的期待。在一场乡村葬礼的不同场合中的哭泣,或出于情,或出于礼,或出于面,当然更可能是三者的杂糅。
首先,最直接也是最普遍的一点是,哭泣为情。逝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人们为生命的逝去恸哭。哭泣是一种强烈的情感的呈现方式,不过,不同文化对哭泣有不同理解,对葬礼上情感的表达力度也有不同的要求。西方葬礼不提倡嚎啕大哭(王晓凡,2009)。在韩国,“泪眼朦胧”通常被认为是深情的表现,因此韩国的儒教式葬礼上哭泣常常贯穿始终;而在日本文化中,克制哭泣往往更多地受到褒扬(崔吉城,2005)。中国可以说是兼有这两种情况:一方面,哭泣是情感的宣泄,而中国人传统上主张中庸之道,“哀而不伤”是儒家典型的审美推崇,情感抒发应克制有节,不宜过度,“节哀顺变”;另一方面,慎终追远的观念下,人们认可“事死如事生”(王计生,2002),葬礼上的哭泣表现了个人缅怀逝者的诚心。因此,中国的文化语境对哭泣没有一致的态度倾向,缘情而泣在葬礼上不受抑制。往往与逝者越亲密、越熟悉的人的泪水越可能是因情而生的。在葬礼上,这种哭泣使得悲哀之情在群体中得到反复强化(王晓凡,2009),人们的情感反复地被感染、被激发。
葬礼上的哭泣也在满足礼的要求。礼即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人伦纲常,人们在生活实践的积累中形成礼俗。传统的乡土中国是一个礼俗社会,人们认同礼俗形成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依据礼俗行事(费孝通,2004)。在如今现代化的浪潮下,农村留存有更浓厚的乡土色彩,乡村的葬礼中仍可以看到礼的痕迹。正如前文提到,中国传统礼俗以家庭为核心,孝道至关重要,因此催生了中国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礼记》等古代仪礼经典记载有详细的丧礼流程与规范,有些对人的心情、容态都提出了要求,其中有很多涉及哭泣,例如闻丧时要尽哀而哭、见宾吊丧时不哭等等;民间习俗也演变出了不少哭号的守则,如传说哭声会使亡魂迷失方向,中国有些地方至今还保持着送魂不哭的习俗(王计生,2002;王德志,2016)。《白虎通》曾这样解释丧礼中对情绪的规定:“情貌相配,中外相应……歌哭不同声,所以表中诚也”(刘喜珍,2009)。礼俗对哭泣行为进行规范,主要是为了让人们践行孝道、遵守伦常,保证社会的秩序。如今乡村葬礼中,尽管哭泣本意也许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孝心,但是孝子们都愿意去遵守“老规矩”,请专门的师傅指导葬礼,对于一些守则宁信其有(郭于华,1992),一些场合中的哭泣也就存在出于“礼”的原因了——哭泣以示孝心或诚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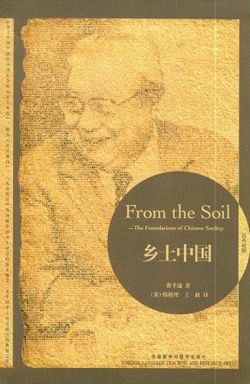
葬礼的排场暗示着一个家族的团结状况和经济水平,一场隆重、声势浩大的葬礼是一个展示家族实力的机会,因而葬礼上的哭声也就与家族的面子产生了关联。面子是社会关系的反映,是家族在村庄中的地位的体现。在我参加葬礼的村庄里,有出殡前举办流水宴席的习俗。逝者家里的男主人负责在院落门口招呼来客,家中女眷多在厨房准备饭菜,村里村外的人来来往往,热闹的程度似乎与婚礼没什么差别——“红白喜事”都是家族成员社会网络的一种展示,都关乎家族的“面子”。若是谁能请来戏班在村口搭台唱上半天,这一家族的地位在村民的心目中就更高了。哭号也是同样的道理。出殡仪仗若是稀稀散散,只有几人低声抽泣,那么家族的惨淡状况人尽皆知,家里人在村人前没有“面子”;而若仪仗人数众多,浩浩荡荡,哭声惊天动地,那么这场葬礼的人员组织、资源消耗、场面营造无一不在证明家族的凝聚力。有些地方出现了专业的哭丧队、职业的哭丧人[1]。因此,哭声的营造有“面子”的需求。葬礼的参与者在集体出殡时的哭号,是家族团结的体现,也是家族面子的需要。
可见,尽管葬礼是死者的生命仪式,但是在中国乡村的传统实践中,葬礼对于生者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生者在葬礼中的哭泣,不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也在满足礼俗的要求、社会的期待。葬礼是家族实力的展现,人们在祭奠亡者的同时,也在为生者的未来铺路。
2018年春文化人类学课程作业
复旦社会学 何舒涵
复旦人类学 裴阳蕾 编辑
参考文献:
Palgi, P. & Abramovitch, H. 1984, “Death: A Cross-Cultural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3, 385-417.
范热内普,2012,《过渡礼仪:门与门坎、待客、收养、怀孕与分娩、诞生、童年、青春期、成人、圣职受任、加冕、订婚与结婚》,北京:商务印书馆。
费孝通,2004,《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
郭于华,1992,《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计生,2002,《事死如生:殡葬伦理与中国文化》,上海:百家出版社。
崔吉城,2005,《哭泣的文化人类学——韩国、日本、中国的比较民俗研究》,《开放时代》第6期。
黄健、郑进,2012,《农村丧葬仪式中的结构转换与象征表达——基于一个丧葬仪式的分析》,《世界宗教文化》第4期。
梁宏信,2014,《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理论述评》,《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刘喜珍,2009,《论传统丧葬制度的伦理根基及其伦理意涵》,《船山学刊》第1期。
王晓凡,2009,《探析中国传统葬礼中的哭泣现象——兼谈中西传统葬礼中的哭泣所反映的文化差异》,《传承》第8期。
李曦淼,2012,《尊崇与权威:汉族女性葬礼中的娘家人——石林彝族自治县大可村葬礼调查》,《民族论坛》第8期。
王德志,2016,《周代丧礼对当代曲阜地区丧葬习俗的影响》,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