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肯尼亚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寒假实习过程中,亲身经历诸多文化冲突。其中最为令笔者感觉疑惑不解的“摩擦”和误解,存在于与肯尼亚人日常交往中的“互惠关系”方面。在文化人类学课堂中关于道义互惠模式的学习和相关文献的阅读后,笔者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过去两个月中的诸多经历,也对于肯尼亚当地文化中的“互惠”思想以及其对于现代社会职业精神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
(一)初来乍到的“互惠”文化冲突
到底实习公司的第一天,我便被长期在肯尼亚工作的同事告知:千万不要对他们太“客气”。原因是由于我的航班延误,到达机场时,公司的司机师傅(肯尼亚人)已经在机场等候我接近一小时了,为了表示感谢,我准备去给司机师傅买一个面包暂时充饥(因为当时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却被一同来接我的公司中国同事阻止了。“你要知道你没有给他买晚饭的义务。”
在同事的解释中,如果这次我给司机师傅买了面包作为感谢,会让司机师傅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如果下次不是这样,司机师傅可能反而会产生负面情绪,长此以往在管理上会产生许多麻烦。
在刚到达肯尼亚的我看来,我认为我的这位同事是名副其实地区别对待了肯尼亚员工,而这样的态度让我一开始非常“摸不着头脑”。因为在中国人之间,尤其是例如公司的司机师傅等,往往都与其它员工有除了工作上的接触之外,较为和谐的朋友般的私人关系。正如我的父母经常会把旅游特产带给公司同事,包括司机师傅分享一样,我认为给司机面包吃,是非常正常的事。
然而我很快发现,这并非这一位同事对于本地员工的“偏见”。几乎所有的同事都经常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下告诫初到肯尼亚的员工不要试图通过“互惠”试图当地员工建立个人友谊。在我的工作中,最经常密切接触的当地员工便是司机师傅和公司一位负责清洁卫生和餐饮的后勤人员。这位后勤人员是一位几乎与我同龄的当地女孩。在“情人节”那天,公司中一位同样新来的男同事,为公司的每一位女同事都送了一朵鲜花,包括公司的后勤女孩。后勤女孩接过花后并没有说“谢谢”,甚至没有露出明显的表示感谢的笑容。
而于此同时,肯尼亚人对于索取认为他们应得的馈赠时,态度直接地令我惊讶。例如在肯尼亚的通信服务门店办理手机卡时,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对我进行了热情的服务,在服务接近尾声时,他问道“你可以请我喝罐可乐吗?这些工作本来我可以不帮你做的。”这样的经历屡见不鲜。
一位同在肯尼亚的中国同事向我们讲述他曾经在肯尼亚的贫民窟中从事发展类工作时的经历。他在一次贫民窟的公共活动举办中,请一位贫民窟的少年帮忙。在工作中,这位年轻人聪明踏实,于是他也产生了为这位年轻人找一份稳定工作的念头。活动结束后,为了对这位少年表示感谢,并建立友谊,他跟这位少年说“今晚我请你吃饭,吃什么你定!”于是,这位少年打车把他带到了整个城市最贵的奢侈酒店。中国同事对此大为愤怒,因为在他看来,这是这位肯尼亚少年想要好好“讹”他一笔,于是他当场便生气地离开了。
在肯尼亚的大型超市和商圈外,如果手中拿着购物袋在路边停留,或把袋子放在脚边时,往往会有一些当地人(通常是来自贫民窟的无职业者)聚集过来,与我进行简单的攀谈并向我索要购物袋中的食物,在有些情况下,甚至直接把手伸进袋子里翻找。这种行为与乞讨者的“乞讨”,即希望对方“行行好”,进行馈赠不同,与强盗的暴力掠夺也完全不同,他们的这种索取中有一种“理所应当”的意味在。

图一:贫民窟小学的穆斯林孩子们与我们打招呼
(二)人类学视角下的“互惠”模式再思考
这一切显然不是中国人坐在一起相互抱怨“当地人不知感恩”“得寸进尺”这么简单而富有偏见的“吐槽”可以概括的。这些跟中国人预期显著不同的反应背后自然有其与中国文化不同的文化逻辑,但这种文化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或者说但却难以名状。直到我读了课程阅读材料 Strings attached 一文中几位人类学家的经历和对此的分析让我感到恍然大悟。在文章中,多位进行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都有类似的经历,即他们给自己所在的非洲当地部落献礼时几乎从未得到过村民的感谢,常见的经历往往是被抱怨礼物不够好。
这实际上体现的是这些“原始”部落对于“礼物”的理解。首先,没有绝对慷慨的行为,礼物被认为是必须有所回报的,因此对于礼物不会表示感谢,因为一份“礼物”的出现并不代表馈赠,而是一次“互惠”。于是受礼者便更多关注于赠礼者需要自己付出的回馈。当他们贬低一份礼物时,一定程度上是试图减低送礼人对回报的期待。这种对于“互惠”不同于工业社会人的理解有其根源:在狩猎部落中,一位成员杀死猎物并给同伴进行分享是他们生活中的日常,这种“互惠“显然是一种义务而不值得特别的赞扬和感谢,是狩猎部落中的经济生活方式。每一位成员都会把自己的猎物分享给他人以及得到他人的分享,部落成员往往都会贬低猎手带回的猎物质量,因为一定程度上对同伴的苛责是用来相互激励保持谦逊人生态度的方式,也是维持采集社会秩序的一种道德机制。
显然,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被批评为”不懂得感恩“的态度对于这些部落的社会生活而言,起到了鲜明的正向作用。
在这一基础上,我对许多之前不能理解的经历都有了新的认识。
“不要跟他们(肯尼亚人)讲情面,(即是你跟他们)讲他们不跟你讲这个的。他们不领情的。”管理司机与后勤工作的中国同事这样评价当地员工。这位同事本人由于社会工作专业的背景,曾经自认为可以与当地员工建立良好的沟通与关系,试图与他们聊聊自己的生活,成为朋友。但事实上效果并不理想。“你为他着想,他是不会为你着想的。”她这样评论。例如在某次下班较晚时同意司机师傅把公司的车开回自己家后,司机便开始经常这样做,甚至在她明确告诉司机不可以这样做时。后勤女孩的情况也同样。在体谅她的个人情况,几次同意她的请假请求后,她不但没有像中国同事预想地那样,以更好的工作态度回馈这种体谅,反而对待上班的态度变得越来越随意。“我跟她聊过好几次,跟她说如果她好好对待这份工作,比如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学做一手中国菜,把公司按照我们的要求打扫得更干净,我们是完全可以给她涨工资的。学到这些技能对她以后找更好的工作也很有好处,但她不会听进去。”在中国同事看来,除了不懂得“均衡互惠”——中国人的“情面”问题外,当地员工也通常没有远见,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没有规划。
总体而言,肯尼亚当地较为下层群体对于“互惠”的理解,正如“印第安人的礼物”那样,往往一个付出需要明确而快速的回报。而对于建立较为长期的合作性的“互惠”关系,例如中国人的”人情“关系,组织中的互利共赢等,通常他们的意识较为淡薄。笔者认为这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肯尼亚当地的历史文化。在笔者的理解中,对于长期合作性的“互惠”关系的认同,或许常常需要来自于高度组织化,经济来源较为稳定因而对未来有较强预测能力,社会成员交往,合作以及利益关系非常密切的社会文化基础,包含着对他人信用的普遍性认可。在这样的社会中,成员对于自己当下的付出在一个并不明确的未来时间点得到回报能有较强的信心,长此以往才能鼓励“均衡互惠”作为一种普遍的,深入人心的概念,成为某一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而肯尼亚作为非洲大陆的一部分,在西方殖民者进入之前处于较为相对欧亚大陆较为原始的社会阶段,没有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活,因此也没有“均衡互惠”思想贯穿日常生活行为逻辑的普遍社会基础。(这只是笔者对于肯尼亚文化中缺少“均衡互惠”概念原因之一的一点简单猜想。并非说较为原始社会中都一定缺少“均衡互惠”概念产生的基础。例如莫斯在《礼物》中对于系北美洲部落礼物交换的分析,便是一种具有期货性质的均衡互惠。)
莫斯在《礼物》一书中,通过将作为现代法律经济来源的古代罗马法典的分析与对原始部落互惠行为的民族志分析进行比较研究,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和道德基础源自原始部落的“礼物-交换”思维。的确,作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和道德基础来源之一的契约精神,从人类学角度看其实是以一种类似“均衡互惠”的概念作为基础的,一方遵从契约给另一方提供某种价值,而另一方也遵从契约在一定条件下予回报。而肯尼亚本土文化中对于“均衡互惠”概念的缺失,则必然导致了面对现代工业社会文化时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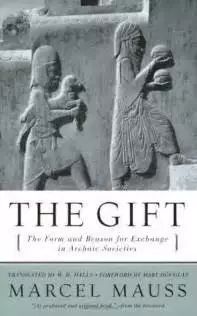
(三)传统社会规范与“贫穷的亚文化”
肯尼亚的中国公司的中国员工们对于当地员工最常见的评价就是“缺乏职业精神”与“没有远见”。这种批评令我不得不想到班费尔德在《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中详细考察了意大利南部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乡村蒙特格拉诺的情况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当地的贫穷是由于村民无法为了发展和获得利益而相互合作、采取共同的行动,这是由于一种“非道德性家庭主义”——“核心家庭的物质利益最大化,并设想他人也都会这么做”的伦理基础导致的。这种伦理导致村民甘心“获得一些即刻的报酬,接受现实和眼前的安排”。
从人类学互惠关系的角度看,这个村庄的村民与家庭成员间有着明确的互惠概念和信心,但当地的文化下来自不同家庭的村民之间存在着由于认为他人也都只考虑“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而对他人做出对己有利行为的可能性的质疑,这就导致了他们不会采取以“互惠”作为行动逻辑的合作从而促使当地的经济发展。
班费尔德认为“穷人常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和生活,某些方式与正式组织的需求完全不一致。”“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班费尔德在这里把对于意大利这一村落居民的观察结论概括为一种贫穷文化的体现。这种论述带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把贫穷认为是不正常的,丞须被改变的现状。但他描述的这种情况却与肯尼亚本地下层群体的情况有相当的可比性。他所说的“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和生活“正是这种没有”均衡互惠“文化传统下的方式,导致了他们难以形成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职业精神,这也正是他们”与正式组织的需求完全不一致”的,“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但对于肯尼亚当地人来说,这一套价值观并不一定是因为贫穷而被”内化“的,相反,这或许是他们固有的价值观。但是,这种价值观就一定会导致贫穷吗?
凯索尔曾在《贫困和底层阶级》中把贫穷归结于一种社会失范带来的社会价值观无序导致的结果。“贫困战争的失败,源于工业所需要的和穷人所能提供的技术和态度的错误匹配。”虽然凯索尔的这一分析是针对美国的贫穷底层阶级,但笔者认为,肯尼亚下层人士在正在经历现代化改造的祖国中经历的贫穷有着非常相似的原因。曾经稳定发展的较为原始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的历史进程猛然被西方殖民者的进入切断,城市在曾经的农田和牧野中突然建立,而随着全球性的殖民主义的衰弱,又进入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整个进程伴随着持续性的社会失范。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是非洲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然而这座城市里存在着非洲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难以数计的贫穷人口世世代代在充满疾病的拥挤街道间勉强为生,由于没有教育资源,也难以找到工作,融入内罗毕的现代社会生活。

图二:非洲最大的贫民窟之一“基贝拉”里的新建住宅和小商店,街道上的广告牌“M-PESA是当地一种有电子支付功能的手机卡,使肯尼亚大量没有能力消费智能手机的人群使用普通手机也能完成电子支付。
凯索尔认为“底层阶级的出现很可能反映出这种价值(维多利亚式工作伦理)的缺失,或贫困人群中越来越多的失范状态,政治制度只有通过再社会化使穷人采取更妥当的行为,成功地修复传统规范的沦落,才有可能取得进展。”然而对于肯尼亚当地人来说,他们的传统规范并非美国人的维多利亚式工作伦理,而是来自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相较工业社会较为原始形态社会的伦理规范。这种规范或许没有“均衡互惠”的概念,或许缺乏契约精神,但其本身是符合他们的历史与社会发展逻辑的。然而在殖民时代西方人的进入切断了这种发展,当下的全球化时代,工业社会扩张到这片大陆并试图改变这片大陆,肯尼亚被迫卷入工业社会时,这种传统的规范成了需要被“改造”和扬弃的东西。
凯索尔与班费尔德都认为处于“贫穷”文化中的群体难以依靠自身完成对抗贫穷的战争,改变的希望来自于外部群体。然而到底如何改变?是通过大量的福利与资金救济直接救济贫穷,还是授人以渔,进行本土文化的改造?是建立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还是将本土文化全盘西化以尽快改变贫穷?这又是另一个需要运用人类学智慧和跨学科思考的问题。
复旦社会学系 张鹤竹
汪醒格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