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及发现问题
复旦大学北区食堂位于复旦大学北区学生公寓内,主要服务于居住于北区的研究生和留学生,以及部分专业的本科生。由于其饭菜口味广受学生好评和推荐,北区食堂的服务范围往往扩大到全校,经常有居住于本部甚至南区的学生长期性的到在北区食堂就餐。北区食堂共有二层楼,一楼主要为中式菜类窗口,供学生点菜;二楼则窗口类型多样化,提供中式菜类,也有西北火锅,麻辣烫,意式面饭,韩式饭菜,以及各地风味小吃等。虽然两个楼层提供饭菜多样程度有所不同,但其就餐配套设施、空间布局设置、工作人员岗位安排、灯光布置特点几乎没有差异。两个楼层有着各自相对完整的结构和运行流程,表现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北区食堂的工作人员由多种不同类型构成。包括餐厅经理,厨师,窗口内负责打菜的人员,负责清理桌面的保洁人员,回收碗筷的工作人员等。而学生“能直接能看得见”的是窗口打菜的工作人员,保洁人员,以及回收餐具的工作人员这三种类型。不同的类型的工作人员,各自分布于不同类型的空间,活动于不同特征的地方。我之所以对此区分感兴趣的,来源于我一直以来对颜色和灯光的敏感。我发现同一餐厅内的不同职责的工作人员穿着不同颜色的工作服,他们的活动场所也被赋予了不同的灯光强度。于是我产生好奇和疑惑:为何负责打菜的工作人员身着白色工作服,而负责保洁和回收碗筷的工作人员身着绿色或褐色等深色工作服?为何打菜的窗口都灯光明亮,而负责回收的窗口里灯光昏暗?这些看似细节和偶然的差异,背后是否被赋予其特定的意义?这些问题引发我继续探讨这其中的机制的兴趣。

二.玛丽·道格拉斯的启示和灵感
在《洁净与危险》一书中,人类学者玛丽·道格拉斯将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清洁与污垢的区分与社会秩序相连加以考察。书中指出,事物的洁净肮脏与否,和它们本身的“洁”与“脏”无关,只取决于它们在人类文化分类系统中的位置。“污秽”就是位置不当的东西。它是分类的剩余和残留,被排除在我们正常的分类体系之外。就像书中所说:“鞋子本身不是肮脏的,然而把它放到餐桌上就是肮脏的;食物本身不是污秽的,但是把烹饪器具放在卧室中或者把食物溅到衣服上就是污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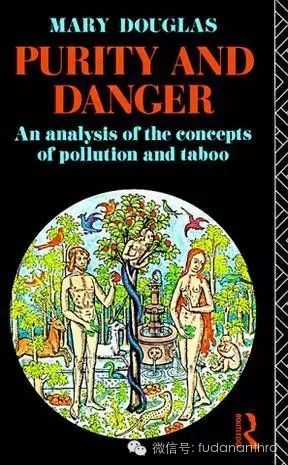
道格拉斯指出,我们现代人的日常活动,也往往带有原始仪式特点,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我们关于洁净和肮脏的医学观念与原始人的神圣观念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其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重建我们周围的环境秩序。而在社会秩序(包括伦理道德)的重组过程中,污染观念、禁忌、宗教仪式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换言之,通过象征秩序的建构,往往能够帮助相应的一种社会秩序的维持。干净、整洁,象征着新的可以由愿望来安排的秩序,如在庆祝新年到来时,家家户户都会洒扫庭除,这样看来,这一切都仿佛是对一种新秩序的期望和许诺。而污垢本质上是混乱的无序状态,但是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污垢:它只存在于关注者的眼中。污垢冒犯秩序,去除污垢并不是一项消极活动,而是重组环境的一种积极努力。在去除污垢、整理杂物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是受到了“要逃离污垢”的渴望,而是要积极地重建我们周围环境的秩序,使它符合一种观念。污垢意味着越界,意味着对现有差别体系的威胁,因而是危险的,必须通过某种洁净仪式来消除它,使一切恢复常态。
而对于那些模糊不清的事物,虽然玛丽·道格拉斯指出它并不完全等同于非正常事物,但她仍然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联系,非正常和模糊在现实中很难区分。非正常是不能融入到已存在的系统中的元素;而模糊则是一种陈述的特性,即这种陈述允许两种解释,它其中也暗含着其无法被清晰分类的性质。人们对暧昧不明的行为的反应表达的是一种期许,即万事万物都应正常遵从世界的治理法则。
《洁净与危险》一书对于我理解北区食堂内所观察到的现象有很多启发,不同职责工作人员有着深浅不同颜色的工作服,不同的场所配置着亮暗不同的灯光,由此带来的明晰或模糊的不同视觉效果,这些是否和我们对清洁的追求和对污渍的避免有关?是否也和我们所希望建构的社会秩序有关?这些都激发我提出假设,以上这些区分可能不是偶然和无意义的安排。
但是《洁净与危险》一书并没有完全能够解释和回答我所想要了解的内容,对于作者的假设、推理以及最终得出的结论,我仍存在几点疑惑。首先,《洁净与危险》一书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假设之上,即:污垢意味着对秩序的危害,人们对此难以容忍。但是,由于社会秩序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太多的冲击使得人们难以有足够精力来一一消灭所有的污垢,为此人们完全有可能把一部分污垢纳入秩序的一部分,用来增加秩序的弹性,将之列为秩序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从而使得秩序的运行更加顺畅。正如中国一些流传很久的谚语:“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污糟污糟,吃了长膘”。中国传统的一些思想并未选择对污垢进行敏感的祛除,而是对其显示一定程度的容忍,并且表达为谚语的力量将之传承,使后代同样接受。
其次,即使《洁净与危险》的假设是正确的——即污垢危害秩序,人们对污垢是难以容忍的——因而道格拉斯提出推论:人们会积极的去除污垢来维持秩序的井然。但是对于这些污垢,人们往往有若干种方式来处理。在积极方面,我们可以有意识面对这些反常事物,并且创造出一个它们能够融入其中找到自己位置的新的现实模式。但同时在消极方面,我们也可以故意忽视它们,不感知它们,转移人们对这些非正常事物的注意力。正如同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眼不见为净”,为了追求洁净,人们不一定是积极的去除污垢,也有可能选择对污垢进行有意识的无视。
第三,道格拉斯认为,事物的洁净肮脏与否,和它们本身的“洁”与“脏”无关,只取决于它们在人类文化分类系统中的位置。“污秽”就是位置不当的东西。“鞋子本身不是肮脏的,然而把它放到餐桌上就是肮脏的;食物本身不是污秽的,但是把烹饪器具放在卧室中或者把食物溅到衣服上就是污秽的……”。但是在实际观察中,我们发现,即使事物处于该处的位置,它也仍旧会被视为污渍,如当就餐者想要丢弃其吃或未吃过的饭菜而将其放置于回收餐具处时,此时这些饭菜处于其该处的位置,但它被放置于此时,它同时也就被定义为污渍;因此,我认为作者也忽视了除位置错乱以外其他影响事物“洁净”与否的因素。
第四,道格拉斯认为,模糊同非正常事物一样,是难以被分类的,无法被划入系统之中,也是对现有秩序的一种挑战,因而也是被人们所要积极避免的。但在现实观察中,我发现,无论是昏暗的灯光,还是深色的工作服,都在试图营造着一种模糊的视觉效果,这种对模糊和暧昧不清的事物的追求与道格拉斯的陈述也有所出入。如果在食堂中存在着对清晰和对模糊的二元的追求,那么这是否仍然与秩序有关?以上这些问题都值得在实际田野观察中继续考察。

三.研究假想
白色这种色彩,在视觉文化中往往表达了一种纯粹洁净的意义,而正是这种纯粹往往不能容忍任何污渍,因而一点点污渍都很容易凸显出来,白色的这种特征能够让人保持一种对污渍的警惕感。因而,餐厅内白色的工作服是为了让污垢看的更清楚,让工作人员注意及时清洗工作服,也让学生感觉到饭菜的卫生清洁,给予就餐者以安全感,维持系统的秩序感;而绿色或褐色等深色工作服,更接近泥土和大地的颜色,它往往更具有包容性,对各种色彩都具有较大的相容,使之难以轻易辨认。绿色和褐色的工作服本身就是对污渍颜色的一种模拟,是为了让油渍污垢看不清楚,因为负责保洁和回收碗筷的工作本身更容易接触到油渍,这样工作服沾到污渍也不容易被注意到,使得他们即使行走在学生附近,学生在就餐时也能感觉远离污渍,感觉食堂环境的卫生和清洁,从而感受到一种秩序感。
同样,打菜的窗口内,明亮的灯光是为了衬托出菜的鲜艳色泽和窗台的窗明几净,以此希望被就餐者关注到,而灯光昏暗是让剩饭残羹和油渍汁液尽量不引起就餐者注意,即使被看到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掩饰住其真实状况。亮度的高低程度不同往往体现对事物的强调程度的差异,也体现其对于就餐者关注与否不同程度的期望。
如果这种推断是合理的,即颜色和亮度的区分都是出于对清洁的追求和对污渍的逃避,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猜想,负责打餐的工作人员总是高声吆喝的行为,有的甚至哼出抑扬顿挫的调子,是为了吸引就餐者的注意,从而在众多窗口中凸显出本窗口的饭菜;而保洁员和回收窗口内的工作人员总是沉默少语,也是他们希望尽量淡化自己以及自己所接触的污渍对于就餐者的影响,如果这一角度的解释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再轻易的把不同职位工作人员的不同言语和行为特征仅仅理解为他们个人的性格不同,而更能够从社会秩序的内化使然的角度来理解。另外,我们也能够推测,出于对清洁的追求和对污渍的逃避,同样是身着手套、口罩、帽子、工作服,但这些装备对于不同职责的工作人员有不同的作用。对于窗口内负责打菜的工作人员,“全副武装”是为了防止自己的衣服上和手上的污渍、自己的头发丝和唾液会污染到食物,从而追求饭菜的清洁;而负责保洁和回收的工作人员之所以“全副武装”,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皮肤和污渍直接接触,避免衣服被污渍污染到。
总结以上假设,我认为,在食堂这一环境下,存在着对清晰和对模糊的二元追求,存在着对污垢的积极去除和消极忽视的二元处理方式,而这些不同的途径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洁净,从而维护秩序,维护的秩序是一种更有弹性更容易维持的秩序。而通过色彩、灯光的强调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体系来建立起与现实秩序的联系。
四.理论意义及实际意义
理论层面上,本文的主要假设是建立在《洁净与危险》一书的理论框架之内,但同时对该书很多观点和结论也提出不同的观点。玛丽·道格拉斯认为,事物是否处于它该处的位置往往能够决定它是否是污渍,污垢危害秩序,人们对污垢是难以容忍的,因而人们会积极的去除污垢来维持秩序的井然。该观点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也有一些内容需要继续推敲。但是本文力图对话该观点,基于初步的田野观察,认为即使事物在其该处的位置,但还有一些因素影响到人们对其清洁的感受不同;当污垢危害秩序时,人们不一定对污渍难以容忍,也有可能将部分污渍纳入秩序范围之内;人们对污渍的态度也不一定是积极的去除,也有可能是消极的忽视。本文提出假设并希望通过接下来的田野观察来验证该假设的真伪。因此,本文所作的研究计划有助于更深刻的了解社会在追求洁净、维护秩序时的多种可能性的方式。通过本次研究有助于对道格拉斯的“洁净-秩序”的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实践层面上,本文的研究结果将为餐饮业营造怎样的就餐环境提供参考。颜色和光亮对于就餐者有着很大的影响,深浅不同的颜色和明暗不同的光亮往往能够带给消费者不同的感受和意义,这一结论早已被很多餐饮业都烂熟于心,奉为准则。但是本文将颜色和光亮的选择与对洁净的追求相连,与秩序的维持相连,力图发现色彩和光亮选择偏好背后的深层的稳固的因果机制,而这一因果机制的揭示对于餐饮业营造怎样的就餐环境能够具有更加有说服力的解释和建议,也有助于餐饮业从业者更加深刻的了解就餐者的个人偏好是如何和维护社会秩序相连的,赋予决策者以社会学的想象力,从而为其多方面的决策提供更理性的指导意义。
五.前期准备工作
在研究之前,我已经在北区食堂多次进行观察,并且作为实际的就餐者,体验北区食堂的就餐环境,感受就餐者日常就餐的全过程,与工作人员进行直接接触,并且在此基础上,已经完成完整的观察笔记一篇,这些都有助于我更好的了解研究对象的社会环境和发生背景,为接下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实际基础。此外,在北区食堂做田野调查时,我已与负责打菜的工作员工、保洁员、回收员、其他就餐同学都有过口头交流,初步询问过他们对于北区食堂清洁状况的感受,虽然还不够具体和全面,但是对于后面详细的调查设计很有启发。另外,在开展正式研究之前,我已查阅一定数量的文献资料,包括《洁净与危险》、《阴翳礼赞》、以及一些有关餐饮业色彩选择、艺术设计等的书籍资料,这些来自于人类学、文学、餐饮业、艺术等不同领域的文献资料对于本文分析色彩和光亮也能提供更准确的多领域的知识补充。
六.方法设计
1.结构性访谈
分别访谈就餐学生,打餐员,保洁员,回收员四类不同群体,请他们列出理想的就餐环境最重要的几个因素,并追问其如何实现这些因素;
要求四类访谈者对北区食堂内环境进行简短描述,特别关注其提到洁净、秩序相关的内容,以及对北区食堂工作人员的相关描述,如有需要,及时追问;
询问四类被访谈者各自对清洁的定义和对污渍的表述,注意其描述清洁或污渍时提到的其他事物,请其举例列出几个洁净的事物和污渍的事物,询问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他们对于清洁与否的感受;
询问学生对于理想的打菜员、保洁员、回收员的形象描述,特别注意其对于清洁程度的不同期望的表述,并追问其原因;
请学生描述出理想的打餐窗口、回收窗口的形象,注意其对于光亮的表述以及对洁净程度的表述,以及对秩序的期望,询问其不同的窗口需要什么形象的工作人员,追问以上这些因素间的关系;
2.情景比较
将学生带往四种场景:灯光明亮的打餐窗口,灯光昏暗的打餐窗口,灯光明亮的回收窗口和灯光明亮的回收窗口,每体验一种场景就要求其简短形容该场景,并询问光亮程度的强弱带给他们的感受,记录其不同场景的不同感受,比较不同场景对于他们的不同的意义。
再将学生带往三种场景:一碗同样的菜,在打餐窗口内,由身着洁净无污渍的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手持递给就餐者,由身着沾有少量油渍的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手持递给就餐者,和由身着褐色工作服、看不清是否有污渍的工作人员手持递给工作者,给他们什么感受,请学生选择愿意从哪位工作人员手中接受饭菜食用。
再将学生带往三种场景:在回收窗口内,当站着一位身着暂时还洁净无污渍的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在回收饭菜,当站着一位身着已沾有大量油渍的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在回收饭菜,当站着一位身着褐色工作服、看不清是否有污渍的工作人员在回收饭菜,询问学生对其分别有什么感受,询问其对于三者洁净程度的比较,以及自己对于回收窗口洁净程度实际的期望。
3.角色扮演
请学生扮演工作人员,分别扮演打菜员、保洁员、回收员三种角色,体验其工作。扮演每种角色时,都允许学生自己选择工作服的颜色,调节自己工作场所的灯光亮度,工作时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及与就餐者的交流方式,允许其使用自己所喜欢的方式来维持本窗口前的秩序。
当学生扮演完三种角色时,请学生谈谈对此角色的感受,询问其当时选择工作服颜色、调节灯光、行为方式、交流方式等不同行动的理由,了解这些选择对于该角色的不同的意义;请扮演角色的学生从说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出发对清洁和污渍再次进行描述,比较其与当初所作定义的不同,以及对秩序如何维持的理解,对就餐者的角色期望等问题。
4.Mapping
让打餐员、保洁员、回收员、就餐者四类被访者每人在一张纸上分别画出北区食堂打菜窗口、回收窗口的位置,以及学生就餐的位置,比较不同被访者群体对于三者相对位置的不同距离,询问这样的位置给予其何种感受;如果被访者不满意于此种位置的现实安排,请他们在纸上画出他们理想中的位置安排;并请每类被访者都在其所作的图上标记出自己以及另三类人群,选择他们认为舒服的位置和相互间的距离,询问其这样安排的意义。
复旦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 梅雪
2010年 本科定性研究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