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 文化人类学 刘嘉玮

《无病呻吟》剧照之一
几周前,笔者在美琪大剧院观赏了法国南锡洛林国家戏剧中心演出的喜剧大师莫里哀的“绝世”之作《无病呻吟》。主人公阿尔贡整日觉得自己病入膏肓,每天都要吃无数的药然后洗肠子,完全依赖于自己的医生。甚至,他要把女儿嫁给自己医生的侄子,以便随时为他看病。当女仆杜瓦奈特向阿尔贡表示出他其实很健康、没有生病的时候,他愤愤地向看似关心他却实际只想要他的财产的第二任妻子说:“她居然无耻到说我没有病!”于是,“有病”倒成了让人心安的言辞,医生也肆无忌惮地以此获取钱财甚至加以恐吓,并不关心阿尔贡的身体。
最后,阿尔贡的哥哥等人设计阿尔贡自己成为了医生,并为他举办了一场“医学协会”的“入会式”。所有人身着巫师般的黑色衣袍,戴着高高的尖帽,反反复复地进行着巫术般的仪式,不断提问着阿尔贡治疗某一种病的方法。阿尔贡给出的答案全部都是“洗肠子放血然后吃泻药”,每每听到这个回答后,“医学协会”的会员们就围成圈作法般地转动,嘴中念念有词地说“他回答得完全正确,他完全有资格成为我们的一员”。最终,阿尔贡念着戏谑的宣誓词,众人一起大喊:“让他放血,让他杀人!”

《无病呻吟》剧照之二
观戏的过程中,Miner于1956年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上的那篇奇文《NACIREMA的身体仪式》(Body Ritual Among the Nacirema)一直在脑海里盘旋着——《无病呻吟》简直可以称作剧本版的《NACIREMA的身体仪式》。
在这篇文章中,Miner通过对Nacirema人奇异的信仰和怪异的身体仪式的描述,展现出人类行为的极端状态。醉翁之意不在酒,Miner描述这样一个“群体”巫术般的身体仪式,却是对美国现代医疗体制的反思——现代人信仰现代医术,就如Nacirema人信仰巫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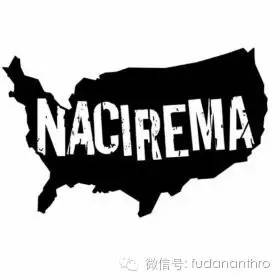
舒茨在《社会实在问题》中有这样的叙述:“对于17世纪的塞勒姆居民来说,巫术不是一种幻想,而是他们的社会实在的一种成分……社会实在包含着信仰和确信的成分,它们之所以是真实的,是因为参与者把它们界定为真实的。”[1]即不论医术还是巫术,它之所以成为真实的,都是因为“受众”的相信。从这个角度讲,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都可以看做一个信仰团体的一种仪式。我们通常并不把现代医术看做巫术,正是源于我们対现代医术的相信。
杰克·古迪在《神话、仪式与口述》中也有过这样一段阐释:“我们用仪式一词指代一种标准化的行为方式(习俗),其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不是‘直观的’,而是非理性的或无理性的。在这个普遍分类里面还有巫术行为,它基本是非理性的,因为有一个过程无法完成的实用目标,或由于完成了其他目标,与病人或参与者所想的完全不同。”[2]在这里可以看到,其笔下的“病人”和巫术的“参与者”完全属于同类。
发现了医术与巫术的奥义与“异曲同工”后,接下来,就要对整个“仪式”做一个讨论了。仪式是信仰范畴中的重要议题,罗惠翾(2009)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仪式的定义,认为仪式就是将信仰付诸实践、表达宗教信念与体验的某些明确的行为方式,它有一定的程序和运用的场合。
仪式有泛化的趋势,早在格雷姆斯(1982)时已被阐述过,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可以被纳入“仪式泛化”范畴的,包括仪式化、惯俗、仪礼、崇拜仪式、巫术和大型庆典等六种类型。
对于仪式的主要指示,彭兆荣(2003)有这样的总结:作为动物进化过程中的组成部分;作为限定性的、有边界范围的社会关系组合形式的结构框架;作为象征符号和社会价值的话语系统;作为表演行为和过程的活动程式;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经历和经验表述。
于是,看待仪式,我们首先察觉到的是比较显性的仪式的象征意义,即从符号论的视角去思考仪式。对于仪式的象征意义,苏格兰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2006)有过重要的阐述。他总结了仪式象征符号结构和特点的三种推断方式:外在形式和可观察到的特点,仪式专家或普通人提供的解释,和主要由人类学家挖掘出来的有深远意义的语境。
特纳认为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具有组合和重组的类似语言的能力。在对恩丹布人的仪式分析中,特纳认为这些象征符号除了指向许多物质器物外,还包括社会存在的基本要求和社会关系。正是因为仪式的社会表现作用,使得仪式象征符号成为了社会行为的一个促进因素。仪式象征符号发起了社会行动,在场域背景里成为行动领域的一股积极力量。它们对个人和群体施加了采取行动的决定性影响,而行为的连续性展演赋予了仪式目的的顺序与结构,达到了社会秩序的重构。如此,象征符号的结构属性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动态变迁。
进而,关于象征符号与社会建构的关系,郑小虎(2012)将其归结为:社会建构——象征符号知识的获取机制;象征符号——社会建构的媒介。即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强化着象征符号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并让该知识具有了一层合法的外衣;而因为有了对意义的共同理解,才有了行动的不断产生,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才会不断的被生产与建构。
然而,宗教仪式并非只是能够把信仰向外转达出来的符号系统。功能主义,无疑是看待仪式的另一重要视角——仪式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其具有一定不可或缺的功能。这个观点从涂尔干开始被不断阐发。涂尔干信徒们的一大共识就是:宗教具有凝聚社会和使人经常确认共同价值的功能。从涂尔干的视角来说,宗教仪式在集体意识、群体团结、集体认同、社区意识、关系、集体表象这些方面都具有功能性的作用。
参见罗惠翾(2009),如今宗教仪式大抵具有这些功能。首先,每种仪式都具有文化濡化的作用。通过参加仪式活动,共有的社会记忆得以传承,过去的历史得以重植于心,一个群体内的人由此拥有了一个共同的集体记忆,因而能够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其次,强化信徒的宗教信仰,参与仪式会建立参与者的信心。宗教仪式把信教者纳入到一个规范化的行为模式和统一的宗教生活之中,以此完成对宗教的基本信仰与教义的重复宣扬,而增强了宗教群体内部的联系和内聚力,并从根本上起到强化与巩固信仰的作用。
并且,仪式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力量。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
再者,宗教仪式对参与者而言能够起到一种心理调适的作用。宗教仪式和宗教象征可以解决个体动机上的冲突,缓解畏惧、焦虑,增强信心,凝聚注意力,调动心理。此外,仪式还有助于缓解无意识动机的冲突,缓解恶意与良心冲突所产生的“犯罪焦虑”。
最后,宗教仪式中的禁忌礼仪可以增强教徒间的认同感。信教者通过恪守各种宗教禁忌,从而可以抑制某些欲望、接受磨炼,并且获得某种圣洁的宗教体验。
不过,看待仪式时符号论与功能主义的视角未必是分离开的,事实上可能相辅相成、相互黏连。根据罗惠翾(2009),仪式行为者通过行动、姿势、舞蹈、吟唱、演奏等表演活动和对象、场景等实物安排,构拟出一个有意义的仪式情境,并从这样的情境中重温和体验这些意义带给他们的心灵慰藉和精神需求。一个仪式,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这种意义感,恰恰是所有仪式的终极功能,它赋予人不同于动物生存的更深刻的意义,将生活提升,使生活摆脱了厌烦、无思想和绝望。

《无病呻吟》剧照之三
《无病呻吟》中最后“入会式”的桥段充满讽刺与戏谑意味,也是直接揭示那种为人所相信的“洗肠子放血然后吃泻药”的现代医术其实与巫术无异的地方。
“入会式”则在仪式范畴中格外具有特殊意义。罗马尼亚宗教学家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中对此即有过比较多的阐述。伊利亚德认为,“转变的仪式和象征意义,表达了一种人类存在特殊思想:即当人类被生出时,他并不是完整的,他必须被第二次出生,这种出生是精神性的。他必须经历一个从不完美的、未成熟的状态转变到一个完美的、成熟的状态的过程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3]而“入会式”则是典型的“转变的仪式”。
宗教仪式标志和促进一个人从一个状态进入另一个状态,而“入会式”则特别地表示着人的精神正在走向成熟并获得启示。对于“入会式”的启示意义,伊利亚德认为其通常包含一个三重的启示意义——神圣的启示、死亡的启示和性的启示。
伊利亚德对于其中“死亡的启示”进行了着重的阐发。“入会仪式的神秘性渐渐地向新入会者揭示了存在的真正的向度。通过把他引向神圣,这就使他担当起作为一个人应当履行的责任……对所有的古代社会来说,对精神灵性的认同是在死亡和一次新的再生中表现出来的。”[4]他阐述道,原始社会中的人通过把死亡变成一个转变的仪式而努力征服死亡,人们终止某种非本质的东西,也即是终止了他们的世俗生命。最终,伊利亚德总结道——死亡被作为一种最完美的入会式,被作为一种新的精神性存在的开始。
可以看到,无论是从人类学、社会学还是宗教学的角度去看待,仪式都是如此必要且耐人寻味的,有符号象征,有特殊功能,更有启示意义。但同时,无论如何,希望我们能够保持对仪式的警惕和思考,保持对相信的怀疑,希望仪式永远不要变成“放血”与“杀人”。

《无病呻吟》剧照之四
参考文献
[1]杰克·古迪,2014,《神话、仪式与口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米尔恰·伊利亚德,2002,《神圣与世俗》,北京:华夏出版社。
[3]舒茨,2001,《社会实在问题》,北京:华夏出版社。
[4]罗惠翾,2009,《从人类学视野看宗教仪式的社会功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30卷第1期。
[5]杨民康,2003,《信仰、仪式与仪式音乐》,《艺术探索》第3期。
[6]彭兆荣,2003,《人类仪式理论的知识谱系》,《民俗研究》第2期。
[7]彭兆荣,2002,《人类学仪式研究评述》,《民族研究》第2期。
[8]郑小虎,2012,《仪式:象征符号与社会建构的探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9]Grimes,Ronald L.1982, Beginnings in Ritual Studies. Washington,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0]Miner,Horace. 1956. Body Ritual among the Nacirema, AmericanAnthropologist 58 (1956): 503-507
[11]Turner, Victor 2006, The Forest of Symbol.Beijing:The CommercialPress.
[1]舒茨.社会实在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第93页.
[2]杰克·古迪.神话、仪式与口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第33页.
[3]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第104页.
[4]同上,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