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7月17日著名核物理学家、教育家、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校长因病辞世,享年86岁。复旦大学社政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潘天舒老师曾因工作关系,和杨福家校长有过交往,听闻消息后和他曾经的老领导周明伟老师回忆起这段往事,不免怅惘,发文以示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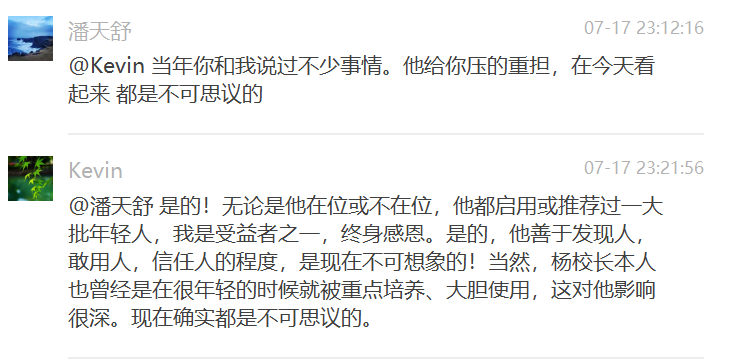
△ 潘天舒老师和周明伟老师聊天中对杨福家校长的怀念

当1993年华中一校长卸任,杨福家校长履新之后,其雷厉风行和不近人情的工作作风,的确令一些学校办公室里常年习惯“舒适圈”办事方式的科员“不寒而栗”。有些事情,我没有亲眼目睹,只不过耳闻而已。为节省笔墨,我只说三件与我工作有直接关系的日常琐事。第一件事是有关与复旦交流学校(欧美)为主的日常信函交流。我原本已经习惯把自己拟好的草稿,送到校长办公室,然后华中一校长或谢希德校长会做些措辞上的修改,偶尔还会改正一些低级错误。这样信件从起草到修改和最后定稿,通常会有一天的时间。然而,杨校长对信函的处理方式,是直接签字,让人送来,我马上寄送或者发传真。这意味着,我草拟的第一稿就是终稿。每次在电子打字机打出稿件,我得看好几遍。有时候,还给英语水平不错的同事看。我深知:杨校长直接签字,对我就是信任。但一旦被他看出什么低级错误,后果不堪设想。如今,我看任何英语文稿,第一眼基本上就能分辨出拼写错误。这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但我还是感谢杨校长,让我养成了这个好习惯。第二件事情与他的时间观念有关。有些外事接待,他不得不出面,说几句外交辞令。但他事先会给个时间限制,一般是“最多10分钟”。有次接待一个有点身份的美籍华人(当时的统战对象),说话喋喋不休,杨校长立马露出不耐烦的样子,还没到10分钟起身就走,可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多亏时任国际交流办副主任的培娣老师,及时以巧言圆场。杨校长不喜欢冗长的各类会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有争议的美谈。最后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离校前完成的最后一项书面作业,就是将杨校长起草一封有关建立复旦医学院的信函连夜翻成英语,发往与复旦有交流关系的国际院校,征求意见和建议。杨校长亲笔手书,论证在复旦这样的研究型大学设立医学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洋洋洒洒好几页。虽然翻译难度不高,但有些医学术语,还是成了我的拦路虎。好在当时美国研究中心的徐以骅大哥(Dr. Hsu),出身医学世家,其父为瑞金医院老院长。他替我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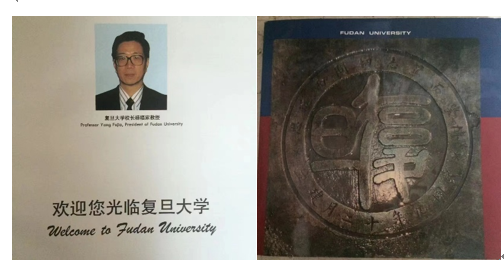

作者:复旦人类学 潘天舒
编辑:胡凤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