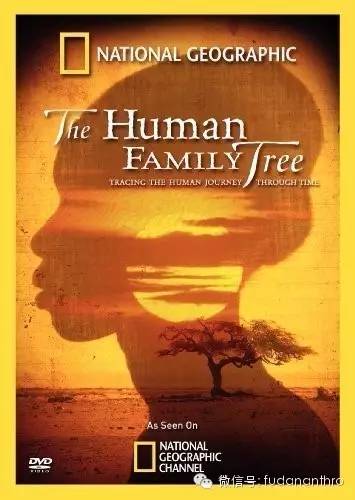
影片《人类基因树》(The Human Family Tree)带领观者进入了一个奇妙而又壮观的人类迁徙与人类溯源的图景,让我们意识到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祖先,所有生命都来自于非洲。即使因为气候的原因人类开始了向不同的地方迁徙,这也不能妨碍世界实为一家的事实。影片表面上从科学的基因角度来探寻“我们从何而来”和“我们为何不同”等问题,实际上其背后有着很深的政治意涵。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正如影片中所说,在纽约皇后区的街角我们就能遇到来自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的人。多民族的结构、各民族的信仰以及日常行为模式的不同使得美国国内种族摩擦与种族冲突不断,美国的一些对外关系与外交手段更造成了美国与其他国家、民族的紧张关系。在这种局势下,影片的主旨——所有人都有共同的祖先,可以被看作一个政治论断,以此促进各民族间的互相理解,达到缓解种族紧张的目的。人们不应该通过肤色等外貌特征来区分所谓的“人种”,因为外貌具有欺骗性,肤色、外貌的不同只是细微的基因变异。所有人的祖先是共同的:科学“亚当”,所有男人的y染色体都从他那儿复制而来;科学“夏娃”,人类基因树的最古老的根。因此,从遗传学上讲,人种并不存在,所谓人种间的差异其实是肤浅、表面、并且不足为信的,也就是说,人种本身是一个“伪”概念。林奈的种族研究即按照肤色把现代智人分为四类:欧洲人(白种人)、北美印第安人(红种人)、亚细亚人(黄种人)和非洲人(黑种人),并且认为白种人优于其他人种。这个研究之所以必须被摒弃的原因,不仅在于从科学上来说人种并不存在(正如影片指出的那样,Genetic Marker才是区别不同族群的最为“科学”的证据),而且在于根本来说由人去分类人本就不可能是客观的,这样的分类早已与民族、文化本身无关,而只是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是一种强烈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分。
同样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还有“民族”这个概念。安东尼·史密斯将“民族”定义为:“具有名称,在感知到的祖地(homeland)上居住,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与众不同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拥有共同的法律与习惯的人类共同体”;不过这一定义只是一个理想类型,“民族”的定义出自民族的精英成员的某种信仰和情感(2011,13)。在我看来,“民族”是一个被建构的“神话”(Myth)。Stone在分析家庭时指出,我们将“血缘”的神话作为基础,“家庭认同”的神话则建于这个基础上,也就是说家庭认同的构建是以血缘神话为基础的(2004,41)。“民族”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将“国家认同”的神话建基于“民族”的神话之上,假定同一民族的人有更深刻的联系,夸大了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为的是达到国家团结、统一的目的。民族神话告诉同一民族的人,他们有共同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和优点。这种特征和优点会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标志,以阻断来自外界的影响,甚至阻断时间对民族的影响,使之成为静态的、不变的、永恒的,因而被赋予了形而上的、宗教的含义。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令民族的这种特征、优势似乎可以得到“科学”上的验证(如颅相学和人相学,以及引申出的优生学)。于是再也没有人会怀疑这本是国家精英成员或其他群体建构的民族神话了。而国家的团结统一并不来自于人们实际上拥有这些特征和优点,而是来自于人们共享了自己拥有这些特征和优点的信念。这种信念是只属于“我们”而不与“他们”分享的。人们会认为自己的民族是“特别”的,甚至是优于其他民族的。“民族”神话因着国家认同的目的被建构出来,现在却俨然变成了一个自足的东西,自身拥有极强的威力。
大多数国家的民族神话只是为了给国家提供团结稳定的环境、给人民提供一种归属感和自豪感,但这样的有关团结和归属的温和目的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地演化成强制性、排外性的目的,使国家的民族神话旨在强迫人民承担固化的角色、排斥国家内可能存在的其他民族,这就产生了一种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我们”对“他们”的强烈排斥。德国政治精英在二战时期就利用精心建构的日耳曼精神的民族神话来对全国人民进行思想上和情绪上的动员,以期使反犹主义得到大范围传播,增强“我们”日耳曼民族对“他们”犹太人——他们被描绘成一个比其他民族渗透性、腐蚀性、威胁性更强、性质最为恶劣的“没有民族”的民族——的排斥,最终给予将犹太民族铲除出德国、铲除出欧洲这一“政治理想”以合法性。
这样强烈的种族主义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异己民族的大屠杀。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种族主义理论、医学实践的进步、现代官僚体系一起导致了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计划的产生。大屠杀并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残暴、野蛮的产物,而恰恰是文明的产物,是现代性的产物。医学实践的进步使得单纯的种族主义发展成——或者说被伪装成——一种科学种族主义,使得野心勃勃的政治精英可以把消灭犹太人的大屠杀称为一次“政治卫生运动”。现代官僚体系则确保了这样的大屠杀可以如同一项社会工程一样得到系统、理性、高效、非人化的贯彻执行(2011)。可以说,只要种族主义、现代性依旧存在,大屠杀就可能再次重演。这是一种可怕的“预言”。像美国这样的大移民国家因此就如同惊弓之鸟,对各种种族主义情绪和行动格外敏感。前不久刚发生的波士顿爆炸案,因作案人的车臣血统和穆斯林背景,而被怀疑是一次有预谋的种族“袭击”。而日本首相安倍企图修改宪法的行为,也让人不禁联想起二战时期日本民族的军国主义和民粹主义,引得周边国家、甚至国际社会一阵骚动。种族主义是如此地与所谓的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时时对“他们”充满了警惕与恐惧。
然而事实上,正如影片所指出的,不管什么民族,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拥有共同的祖先,没有一个民族是高于另一个民族的。其政治意涵,或者说政治目的,就是告诉人们:我们都是同一个家族的人,不应该互相残杀。没有“我们”与“他们”的区别,有的只是大写的“我们”。不过,影片这种基因上、生物上所确立的平等是否意味着真的政治上的平等,是否意味着人们就不需要自己的民族身份(因而都是“国际公民”)?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于第一个疑问,如果没有“民族”,那么现代国家的根基就会被动摇。并且,不能排除有的政治野心家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帜实行民族主义“侵略”的可能性。对于第二个疑问,找寻自我的身份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身份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尤其是对那些离开故乡、融入新文化的人来说。没有民族认同,人们就觉得自己失去了“根”。因此,即使人们“身体上”平等了,文化上的阻隔也仍然存在,这种文化阻隔使人们倾向于使用“族裔中心主义”的视角来评判其他民族的文化。而极端的族裔中心主义又会演化成阴魂不散的种族主义。所以,对于“他者”的文明,我们应该要抱持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承认任何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与文化,社会的发展或进化不存在程度高低的问题。吉尔兹认为,考察其他民族时不应该掺入自己所在立场的道德观、价值观等观念,带着自己的推测与文化偏好,难免会与所见所闻有强烈的抵牾。“我们的观察不是绕过屏障去观察,而是穿过屏障去透析”(2000, 51~55)。观察者应坚持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社会研究的价值中立立场,通过理解当事人的主观意义(而不是从自己的偏好与价值立场出发)去理解他们行动的意义、理解他们眼中的世界,避免混有主观偏见的“想象”。当然,这样一种对于异族文化、对于“他们”的理解不会而且不可能是完全的,也不可能是普遍的,因而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地方性知识。
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越来越越趋向于多元化,并且人与人不相往来也不再可能,这就造成了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之间由于差异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知识可以是地方性的,文化可以是地方性的,但是,我们看待文化的眼光必须是世界性的。带着本民族的地方性知识来看其他民族的地方性文化,难免会做出想象和臆断;而带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来看本民族的文化,又容易产生“自我中心主义”,即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任何不同民族的文明之间的交流都需要一种“他者”的视野,使人们不仅仅从内部来看待本民族的文明,还可以从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文明;并且,作为“他者”而提供不同视角的另一种文明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这样,不同文明间便可以避免互相“妖魔化”或“刻意美化”,从而形成持续的对话,两者甚至能够有区别地融合在一起。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如此吧。
总而言之,“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依旧继续存在着,但是这并不阻碍民族间的交流与互动;不如说,正是由于区别的存在才使得这种交流与互动更有意义。而影片所发出的“基因上人人平等”这一震耳欲聋的论断,则给了各民族一个平等看待“我们”与“他们”的突破口与路径,而这种平等性、世界性的眼光正是可以于“我们”所共享的。
复旦社会学郭巍蓉
2013年春
参考书目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英]齐格蒙·鲍曼著,杨渝东、史建华译:《现代性与大屠杀》.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
Stone, Elizabeth.2004. Black Sheep and Kissing Cousins:How Our Family Stories Shape U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