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ground
Introduction
本书作者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Marilyn Strathern。她出生于1941年的北威尔士,先后在Girton College,曼彻斯特大学,剑桥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长期的田野研究,关注英国的生殖技术。她是一位高产的人类学者,对亲属关系、性别、生殖技术、审计文化、遗传技术、法律、女权主义都有涉猎。这本书《礼物的性别》(The gender of the gift)是部名著,出版于1988年,同时这本书也是一部反思之作,以女权主义方式引出一种对当代西方本土文化的批判。本文是对书中部分内容的梳理。
原文出处:
Strathern, Marilyn. 1990. The Gender of the Gift: Problems With Women and Problems With Society in Melane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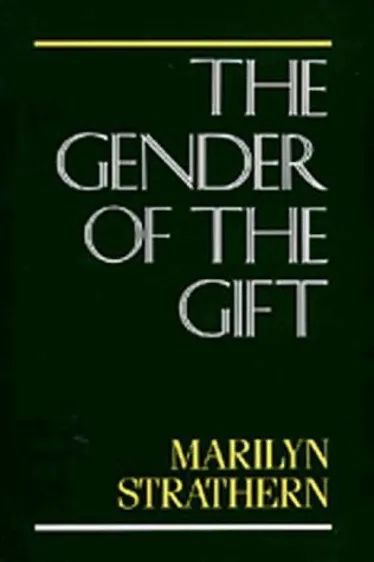
第一章开篇指出:虽然当前美拉尼西亚民族志的一些研究很出色,但是这些研究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正是自己分析的“敌人”。当科学、常规、规律运用于现象世界合理化的过程中,科学范式要求用更专业性、非理性、简化的方式去承担解释的重任。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复杂的,人类学该如何激发和产生一种新的分析方式?作者认为要把控两个方面,一个坚持“持续的”观点,另一个是让这些观点看得见。所以,这本书对美拉尼西亚的叙述可以从三个关系着手:我们-他们、礼物-商品、人类学-女权主义。“我们-他们”是一个介于西方和美拉尼西亚社会之间的社会性问题,不能简单用西方女权的观点来分析;“人类学-女权主义”意味着人类学对美拉尼西亚的知识建构并不是理所当然的;“礼物-商品”的差异可以被理解为用于人类学、女权主义的抽象思考。
分析案例的目的不是用本土的、同行的概念来取代西方社会施加的概念,而是根据他们特定的情境来表达当地概念的复杂性,通过分析建构知识语境来展现本土知识本身。跨文化分析的目的不是为了假设我们与他们的不同,而是分析他们的背景,那个能自成一体的、自我参考的整体。
女权主义学术和社会科学具有相似的结构,都不以自然科学模式为基础,而是以竞争为基础,发现彼此共同的观点,以及可以取代的观点,女权主义对探究的相对性更兴趣,对能够改变世界的方式充满兴趣。社会科学多种观点不断新变化和推广,每个观点都对整体有贡献,描述是不同观点构成的。题材也可以有自己的视角,这使得学者和知识对象建立距离感,从而建立那种以主体无法获得的独特的“第三级理解”。女权主义的内部视角是多元的,如果只将其面临的风险看成是为女性利益的发声,那么这种对待女权主义的视角则是单一的,而“利益”在知识建构之外。
作者认为女权主义之间占据相似的地位,又保持各自的立场,彼此之间形成内部的联系,构成了“一个自我参照的思想体系”,通过多元而非整体的形式来应对普遍性的问题,这种多元愿景将社会作为一个多种、不可调和的利益复合体。
两性之间的不平等被解释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对此女权人类学家也有很多争论,有些争论趋向于形而上的层面。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阐述是文化或社会本身,性别关系是一种社会安排,取决于如何看待文化和社会,身体的差异更容易被视为对理性主义世界的挑战。Hutt(1972)认为虽然性别差异是无可争辩的生物事实,而对性别的差别对待则是一种社会决定。西方人思想中习惯在实践中将性别平等认为是对“没有区别”的表达。人们虽然会认为这些社会安排是来自传统和习惯,但是社会安排可以与现实达成协议、公约,甚至可以为公约寻找理由,以成功处理关于环境、生物学、人性不能妥协的情况,差异是存在于事物之内,应该根据事物内在品质的比较。每一类事物给社会提出一种简单的选择,适应惯例以反映内在属性,或者按照惯例克服他们。但是还有第三种可能,社会习俗与不可简化的自然事实达成协议,重新建立惯例。
女权主义学术与古典人类学都认为:世界各地存在的无数社会组织形式是可以相互比较的。这种可比性是西方组织经验的和知识的明确手段,其假设基础是: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的同源物。社会被认为是具有自己特殊特征的实体,每个实体都在内部组织起来,由自身固有的属性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来自群体的内在属性,社会不仅表现出他们之间的自然属性相似,而且还是一系列内部自然的差异,这些差异成为个人行为的背景.从对Hutt的第二个批判中,“社会”也可以有不同的争辩,但仍包括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人们安排的是差异而不是相似之处,是当观察者准备在其他人的观念中识别出与她或他自己的观念相似之处时,才会挑战可怕的种族中心思想。事实上,社会是问题解决的机制,也是创造问题的机制。社会既能克服个体间的自然差异,也会与所处的环境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对男性和女性都存在问题。所以社会不是我们想象的用自然制造的东西以扩展人类潜能的技术隐喻,所以人类问题真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吗?
以女性为例,女性问题不只是女性的问题,女权主义人类学提到的很多问题都涉及到人类学家关注的各种关系和相互关系,坚持男性和女性的差异以及被概念化的方式,这样的结构在社会中是可变化的,一切都是建构的,因为社会习俗和事物内在本质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结构的自然性、非任意性的关系,以及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些都需要被关注。所以对男性和女性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否则两者都无法理解。
新一波女权主义浪潮开始后,处理男性和女性的差异等同于对所有关系的处理,不能单独只考虑一种关系。高涨的父权制概念引发我们对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思考。社会习俗被入认为只包含一种性别,而不是另一种性别,由此揭示了双重的任意性:社会是习俗,而男性是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习俗。女性在所有社会中的问题需要从社会是什么样的,以及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两个方面回答。
作者认为女权主义和人类学的学术支持对调查世界的性质有不同的方法,女权主义与主流人类学并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为权力关系的研究和本土化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女权主义本身是一个暂时的定义,会遇到其他学者的阻力。人类学和女权主义之间相互影响,人类学有一个神话,对女性、男女关系的研究兴趣必然要涉及女权主义的立场,而且女权主义也发明了他们的研究。打破神话,人类学的研究要重新检验,检验那些关于社会本质、主导机构、权力关系、人性假设与特定利益的关系,或者要说明这是谁的观点,识别这些观点可能会导致对社会立场的事后识别:观点之间的差异和矛盾被转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使其成为对立的,不带有男性偏见,对分析内容的信息源头也要质疑。
虽然女权主义和人类学的内部、外部的建构都不是同一模式,但是人类学为女权主义主义提供了经验,如,对非西方社会男女关系的分析不能解释西方经验;不同的观点在同一时间内并存;经验的多样性被保留为真实性的标志。人类学也试图与多文化、多宇宙学的关系多元化,也在适应女权主义。
在第三章几内亚高低的性反抗这一节,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部分联结”(Partial Connections)。这里先阐述了一个隐含实践:从某些核心研究中延伸出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以源自该核心研究形式成为比较分类的一般轴,然后观察者调查一个地方相关的关系是否在其他地方成立,例如Meggitt的研究。比较分析是将这些相关性去中心化的,并不强调文化先由哪个社会产生。Meggitt将高地人的男女关系描述为“普遍的攻击性”,Langness还将这个关系扩大到战争和政治对抗。这些人类学家虽然尝试将“女性”与社会结构相结合,但是这种结合的张力是建立在对这种结构的想象上。50年代Read对Gahuku-Gama的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观察者构想的社会结构与Gahuku-Gama的集体生活概念之间存在滑移,因为西欧学者对文化的理解中,文化是生产、技巧、媒介,是驯服自然世界和被创造出来的产物,所以研究者将这中观点用在当地文化的解释中,而且将文化简化为男性化。这使得我们需要对研究者的“主观经验”质疑。
对性别认同的研究是一个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但是也被研究者用来解释桑比亚的性别问题,但是这不同于美拉尼西亚人自己对性别的丰富想象。如果从西方男性的阳刚之气和女性气质的价值观分析,整个美拉尼西亚都存在着“人造的”仪式——男人是人文化产物,女性生来如此就是这样。这种观点的缺陷是未能认识关系的性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对比来构想的,但是对比的意义是什么?排斥和反对构成的权力关系是什么?作者在分别评判了Read,Bowden,Tombema Enga,观点之后,将视角转向性别分类系统的隐喻基础,回顾了1970年代男性和女性的分类模型,性别关系是建立在某些实体界限基础上,这一时期的人类学研究中,女性作为社会行为者可以直接将男性、女性概念化为男性的社会或文化建构,这个“社会”一方面是“女性”,另一方面是社会性、集体生活。
西方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分界线在1970年代表现为对公共-家庭,政治-法律的分界的延伸,政治被等同于男性领域,其实政治是一个权力关系和价值等级的系统,必然包含男性和女性;家务与女性事物是等同的,家庭领域被解释为内向型的公共领域。西方对公共和家庭的性别归属的划分,使性别差异作为不同类型生活之间的差异,将“社会”等同于公共社会性意味着将“家庭社会性”从社会中排除;西方文化对男性的理解是一个男性“领域”必须与男性利益对话。
从这样的思考维度去思考美拉尼西亚的民族志研究时,作者列举了美拉尼西亚在70年代的三项研究,案例中“社会”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原本有男性主导的传统的“公共”机构的社会也在发生变化,当地人的价值观并不一定与外部世界是对立的。女性参与地方事物的社会性质被显示出来。Hargen的女性并不是“不完整”的人,儿童也不需通过男人的职务转向“完整”。
推介者:复旦人类学王涛
编辑:潇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