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学期的文化人类学课程中,我最喜欢的是亲属关系这个模块。具体而言,我尤其对潘老师所介绍的系谱图(kinship diagram),以及代表不同时代和理论流派的美国人类学家施耐德(David Schneider)和英国人类学家卡斯腾(Janet Carsten)对于系谱图的批评与发展感兴趣。
在了解人类学以前,我对于系谱图的全部认知来自高中学习的生物知识,即以人类常见遗传病为内容(有时也会涉及果蝇、猫、各种植物)、以一对相对性状(或多对相对性状)的显、隐关系设定父母本的表现型或基因型、进而推算其代后的表现型或基因型的考题。而考学压力下,我从来没有质疑过系谱图的绘制方式及其透露的预设:一个人的父/母是可以确定且以遗传物质的传递确定的,父代/母代/亲代/子代等包含亲族的称谓等同于遗传物质传递的代数,人类和其他有性生殖的生物均适用于系谱图……因此,在了解早期人类学家(如摩尔根和马林诺夫斯基)以系谱图确定“异文化部落”成员间的生物亲缘关系、再以此研究他们对应的社会亲属关系、比较不同文化的亲属制度可变性时,我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就和高中的系谱图一般,不论当地人(或者果蝇/猫/植物)是否承认,都存在这些生物学事实,都存在于系谱图之中。
施耐德的《亲属研究批判》(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对于系谱图的批判恰在于此:为什么亲属关系一定与繁殖有关?为什么亲属关系被认为是“生物”的基底加上“社会”的构材?联系文化相对主义,施耐德是在点明欧洲人类学家自身的文化,反对他们将这种文化投射到世界各地的所有民族。施耐德所指明的系谱图预设是我从未想过的:第一,人类学家假设了亲属关系与包含性关系的生物过程有关,进而把亲属关系的概念强加在他们的数据上——全世界的“母亲”都是“母亲”,所有的母亲都可以通过控制变量(都生育孩子)来进行比较;第二,人类学家延续了欧洲文化中的“血浓于水”,即血缘关系是一种共享生物遗传物质的关系,把substance(血缘)和code(共享血缘的人应有某种行为准则)结合在亲属关系中。施耐德实际是在探究人类学的母题——“自然”与“文化”——自然和文化是界线分明的吗?自然是普世的吗?文化是附在自然之上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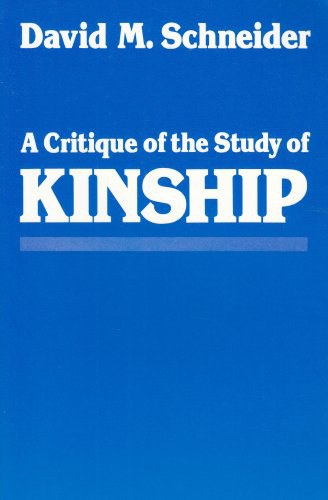
如果说施耐德提出了这些疑问,给出了“我们不能翻译或解释一个女人和她所生的孩子之间的每一种关系,除非通过详细研究当地人如何概念化、定义或描述这种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在文化背景下构建这种关系”(Schneider,1984:200)的研究方向,那么卡斯腾的《炉灶的热度》(The Heat of the Hearth)就是以马来人的田野案例解答了施耐德的疑问,突破了“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尽管马来人同样重视血液(blood),但“血液”是不断形成、不断转化的——这取决于一个人住在哪间房子、每天与谁同吃一个炉灶里的饭。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马来人强调母亲及其后代的密切亲属关系——孩子由父亲的种子和母亲的血液创造,母亲的乳汁也是母亲的血液(因此兄弟姐妹的血液被认为是相同的),母亲的血液来源于她吃的饭(因此分享母亲在同一炉灶里做的饭也意味着分享了共同物质)。亲属关系不是给定的实体(自然),也不是附加的意义(文化);亲属关系是一个过程,它通过分享食物、住所、友谊等等在日常互动中被构建和赋予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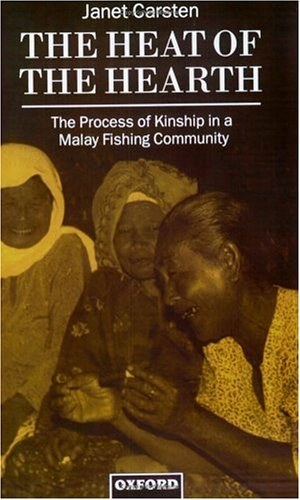
回过头来看高中学过的遗传系谱图,我意识到一切都不再理所当然:清晰的横线、竖线连接的圆圈、三角形只在以遗传物质决定的亲缘关系中存在,只在以认识并推崇“科学”“生物遗传”知识的社会中存在,固定的线条也直接把亲属关系当成了事实而非不断形成的过程。此外,通过以同样的系谱图表示不同物种的亲属关系,系谱图更是在把某些人认定的亲族关系和社会制度(比如能确认父亲是谁的单配偶制)移植到其他物种。例如,高中老师曾和我们强调,果蝇的系谱图不代表某一个个体和另一个个体有性繁殖,而代表一类具相同基因型的群体和另一类有性繁殖(因实验为提高成功率会放入许多只有某种相同基因型/表现型的果蝇),但这种强调恰恰体现了系谱图蕴含的人类亲族预设。
对系谱图的上述重思是我在这学期课堂上的“aha moment”。重思既在于自然与文化的分野,也在于默认从属于自然的生物学与默认从属于文化的人文社科的分野,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能拒斥对于生物知识生产(例如系谱图)的反思和研究。
作者:陈唯伊
编辑:高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