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erson,Elijah.2000. Code of the Street: Decency, Violence, and the Moral Life of the Inner City. W. W. Nor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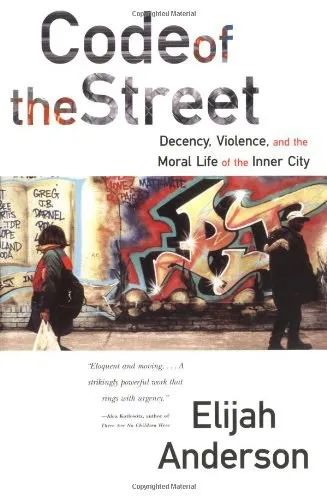
本书写于1999年,作者Elijah Anderson是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和非裔美国研究资深专家。他在美国费城的市中心贫民区进行了为期四年的田野研究。这本书基于两个城市社区研究而形成的民族志文本——一个是黑人社区,他们非常贫困;另一个是种族混合社区,是中产阶级的地盘。作者的关注重点是人际暴力,而他的解释核心要点则是一种社区街头文化。

作者:Elijah Anderson
(一)同一条街道的两种文化
Germantown是费城的一条主干道,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在路的尽头是一个种族混合社区。在这里,似乎曾经割裂的种族矛盾只不过是新闻报道为了博人眼球设置的虚假标题,黑人与白人同时出现在餐厅里并排坐着。但在这幅看似融洽的画面中,作者却有一些敏锐的观察。在餐厅外,黑人男子开着Range Rover,两位盛装出席的黑人女士从一辆Lexus走下——奢华的轿车和精致的装饰似乎在向全世界宣告着自己中产阶级的身份。而反观他们旁边的白人中产,则是开着老旧的车和朴素的衣服——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证明。来自保安更多的关注也昭示着黑人所面临的刻板印象,这是金钱收入无法打破的现实。
而Germantown沿途的另一个黑人社区里,黑人面临的是明面上的打击——去工业化带来的更少正当收入来源。作者展示了这个大型社区面临的社会衰落,贫困、少女怀孕、毒品横行和街头暴力以及经济衰退。作者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同在一个大路上,两个社区会出现如此不同的城市景象?颇具洞察性的是,作者描绘出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符码(code)来解释两种不同的行事逻辑,从而挖掘出造成不同社区景观的结构力量。

(二)街头(street)法则与文明(decent)准则
Anderson围绕着公民社区生活的两种准则对人群进行区分。一种是流行于社区街头的实操性的非正式法则,另一种则是带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文明准则。
Anderson(1999: 33)将街头文化定义为“一套管理人际公共行为的非正式规则,特别是暴力行为——这为之提供了一个理由,让那些倾向于侵略的人以一种被认可的方式引发暴力冲突。” 这种街头姿态的全部意义在于人们知道,“如果你惹我,后果自负。别指望法律,别指望警察,只有我和你”(Aderson,1999: 300),这就是街头守则的精髓。事实上,笔者认为,街头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与文明准则相辅相成的,街头文化的形成恰恰依靠于中产阶级文化,因为它正好是中产阶级文化的对立面。可以说没有中产阶级文化就没有街头文化,通过与中产阶级文化的区分,街头文化塑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符码(code)。
作者描述了文明和体面的(decent)家庭,将他们的孩子培养成以目标为导向的人,旨在“建立美好的生活“以及“用你所拥有的东西来达成这一目标”。可以看出,所谓的文明准则是一种主流价值观,它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努力有所作为。而街头文化则将游戏人生当成一种美德,而将回归家庭、认真学习等当成是一种对街头的背叛,同时还会对这种背叛诉诸暴力。在街头文化的世界里,尊重是核心,而暴力——一种能凸显男子气质的方式,往往是赢得暴力的直接途径。男人需要通过街头暴力展示自己的勇气和能力——我能够为自己负责。书中展示的Malik和Tyree的交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学生”Tyree面对街头男孩Malik的嘲讽和挑衅,往往只能选择接招,进行一场暴力斗殴,而正是这样的暴力使得他终于融入街头,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事实上,为了能够在街道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人们需要具备一种“编码转换”的技能。特别是来自市中心的男性,他们需要隐藏自己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而使他们能够在贫民内城区生存。例如,一个文明的学生在走路时会把书藏在夹克下面,出现在街头,因为书本的出现会让他在街头上不受尊重。这也是Anderson一直强调的,采用街头法规是一个个人层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要么完全或部分地接受街头文化的规范,“要么至少学会按照规则来表现自己”(Aderson,1999: 33)。

(三)家庭:内城社区最后的救赎
作者展示了这个大型社区面临的社会衰落,如贫困、少女怀孕、毒品和暴力以及经济衰退等问题,同时,作者通过大量个人故事展示了黑人社区最后的救赎,那就是家庭。家庭通过亲属关系以及代际之间的相互支持,使得摇摇欲坠的个体得以穿过这些黑暗。
首先,家庭的基本维度是两性关系。而在这个贫困的内城社区,两性关系被视为一种获得“尊重”的手段。对女性的占有和戏弄被视为男子气概的体现,而对女性或家庭的归顺则被视为一种“娘娘腔”式的软弱。在这里,男性行为,如占主导地位、强壮和智力,被描述为男性生物性别有关。内城青年自我实现的途径被阻止,他们无法像在那个中产阶级社区一样获得一份得以养家糊口的工作,相反,他们只有靠走私毒品赚得足以支撑起其尊严的钱财。相比之下,情感、关怀、从属的女性气质与女性的生物性别有关。在两性关系中,征服女性被视为一种男子气概的体现,“对许多男孩来说,性是当地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Aderson,1999:176)。而这种征服往往带来大量怀孕现象,而男生们往往拒绝回归家庭,从而造成孩子父亲角色的缺失。实际上在中产阶级青少年中,性关系中的剥削与不平等也很常见,“但大多数中产阶级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更感兴趣,他们知道怀孕会造成什么负面影响”(Aderson,1999:149)。相比之下,正是由于内城贫困区的青年们遭受着结构性暴力,“他们没有希望看到一个与今天有很大不同的明天,因此,他们觉得未婚生育没什么损失”(Aderson,1999:149)。
未婚先孕的女生们如果无法从男生(孩子父亲)那儿获得支持,那么,家庭关系网络则是她和孩子的支持。其中,祖母往往扮演着一个家庭中重要的角色。作为家族中最年长的女性,一方面她们能够为未婚先孕的女性提供一些生育知识支持,另一方面她们在社区中拥有的人际关系网络持续形成一个公共安全网,但这张网已经在普遍失业和毒品经济泛滥的背景下岌岌可危。
在奴隶制和后来的佃农制度时代,当黑人普遍无法实现经济独立时,祖母往往是一个英雄人物。黑人女性相比于黑人男性往往不被视为对白人男性的直接挑战或威胁,因此,她们更有可能承担起在必要时挑战白人权的角色。时间推移到今天,随着制造业工作的流失,毒品和暴力文化进入贫民窟,黑人祖母再次被要求承担起她的传统角色——她们需要承担起照顾被自己父母抛弃的孩子的责任。在这种传统角色中,“颇具浪漫主义地,她可能真的被视为一个无私的社区救星,她的角色可以被比作一艘救生艇” (Aderson,1999:221)。祖母的社会预期角色是正面的,符合文明准则,更接近于主流价值观。但作者看到越来越多的祖母们正在与街头文化融合,“祖母偏离传统角色的程度一定程度上表明这种社会类型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残酷现实和持续贫困的受害者。它也可能表明社区培养能够在更广泛的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公民的能力正在减弱”(Aderson,1999:221)。
(四)讨论:个人选择还是结构暴力?
那么这种文化符码的选择,是个人偏好,还是一种结构性暴力使然?这是本书最后一章想要探讨的话题。作者描述了一位刚刚出狱的街头小子试图“改邪归正”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恰恰打击了新自由主义话语对贫困社区的诠释,直观地揭示了街头准则背后的结构性暴力。
Robert从监狱中出来决定从事一份合法的正当工作,这个消息让他的兄弟们大为震惊——实际上,牢狱之灾在街头文化里是一种荣耀——代表着强硬、勇气,能够为他赢得街头的尊重。但Robert的转变动机也点出了作者想要讨论的话题,这种街头生活真的会让这个社区变得更好吗?真的能让他们过上美好生活(good life)吗?诚然街头文化能够让他们在社区受到尊重,但这种尊重更像是一种虚假的繁荣,他们依然需要靠买卖毒品挣得足以维持这份尊重的金钱,而家庭也依然飘零破碎。这种文化也会形成一种街头小子的再生产,街头家庭的教育更可能让这个家庭出现下一个街头小子。笔者无意否定街头文化的价值,事实上这种亚文化的存在代表着一种文化多样性,笔者想要说明的是,正如作者呈现的民族志材料想要表达的那样,街头文化背后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使得这群街头小子不得不走向街头,他们并不是主动选择了这种文化,而是一种去工业化和社会不平等组织的绑架。
Robert的转型案例证明了这种绑架。他出狱之后找到了一个在水果摊的工作,一方面他面临着街头男孩的挑衅,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监管和查阅证件。当他走向新生活时,“他也进入了Victor Turner所说的‘阈限状态’,在两个群体中都变得有些边缘化”(Aderson,1999:300)。当他向文明的生活过渡时,他在街头失去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信誉支持(尊重)以及保护。同时,在主流价值观里,他也面临着种族刻板印象以及种种由此带来的阻碍。Robert的经历可以作为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窥探出由于结构性暴力的存在,从街头到文明世界的转变是多么困难。这也恰恰反击了新自由主义将街头文化诠释为个人选择的观点,事实上,这些街头小子早已失去了平等的个人选择自由。
作者:欧阳江影
编辑:唐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