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zfeld, Michael.2014.Engagement, Gentrification, and the Neoliberal Hijacking of History. Current Anthropology 51:259-267
前言:“历史遗产保护”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全球的城市改造现象往往被视为“政治正确”的行为——没有人会明面上否定保护自身历史的价值。但抽象的“历史”往往潜藏于现实的“生活”中,对城市的改造也意味着对日常生活的强劲干预。“遗产”概念本身交杂着亲属关系、财产、住宅等特定文化关系,而面对强势的民族国家公共政策时,这些往往显得微不足道。本文作者Herzfeld以批判性的视角审视“历史保护”,通过将士绅化与对公共知识管理的批判并置,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问题,“历史”是谁定义的“历史”?保护的是哪个“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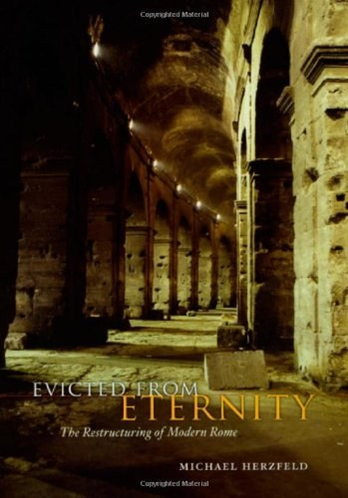
一、争夺“历史遗产”:公共权力与私人空间的冲突
历史遗产保护是一个多重价值观的交界点。从考古意义及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历史保护是一种居于道德制高点的民族历史财富;对于承包遗产保护的房地产商来说,这是一个历史商业化的好机会;而对于居民社区来说,这是一次对日常生活的颠覆。遗产本身往往存在到两个冲突的身份,一个是用于构建公共共同记忆的“历史遗产”,而另一个则是涉及公民居住权等具有法律意义的居所。从这个意义上说,“遗产”并非一个隔绝文化的“事实”(facts),而恰恰是一种文化性的“选择”。是谁选择将这里定义成“遗产”?
民族国家常常需要选定一种文明作为民族秉性的象征,与之配套的便是将体现这一秉性的文化载体划分成历史遗产,并将其“改善”(improve)为足以唤起美好公共记忆的场所——毕竟鲜少有人愿意承认一堆破烂垃圾代表着自己的历史。Herzfeld尖锐指出,与“改善”恰恰相反,这批居民往往在“士绅化”改造过程中被无情地丢出他们原本的生活轨道。我们可以毫不留情地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城市空间的清洗(潘天舒,2017)。而“遗产”的名号带来的收益不仅是公共记忆的构建,同时还有十分直观的经济收入——“古镇经济”就是最好的证明。老房子被贴上了“传统民俗”的标签,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猎奇的游客。在“民俗”神话的笼罩之下,与之相伴的还有不断上涨的房价。Herzfeld尖锐的指出,在这场公共权力与私人关系的互动中,最明显的利害关系便是经济价值和其他价值的角逐。我们通常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导经济意识形态反对当地人民的利益,支持投机者和官僚的利益,将居民的生活伪装成“改善”和“发展”的个人需求。作为历史遗产的城市空间成为民族国家、经济主体与居民的争夺之地,公共权力与私人空间的冲突在“士绅化”过程中凸显得淋漓尽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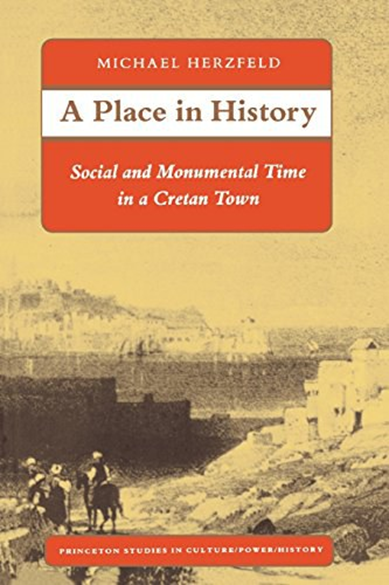
强劲的官方叙事恰恰也成为了一种弱者的武器。事实上,居民们往往通过对住宅历史意义的解读,使其在这场围绕着民族国家公共历史记忆的改造中占上风。Herzfeld在文中举出了希腊人的例子。对于希腊的旧住宅,那些希望拆除它们的人称之为“土耳其式”(在希腊民族主义言论背景下,这是一个贬义词)的房屋,而那些认为想让自己的住宅能够得以保留的人则会采用“威尼斯式”(也因此是“西式的”)的标签。房屋确切建造历史的模糊性使得居民得以在“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与“作为高雅遗产进行保护”之间进行选择——而这也恰恰再次证明,遗产的界定本身是一次文化性的“选择”——同时作者也警醒我们,这种选择的依据时常被西方主义所左右,而非基于本土化理解。同时,Herzfeld也指出,这种对自身所属文化的宣称,实际上可能造成种族及其文化的割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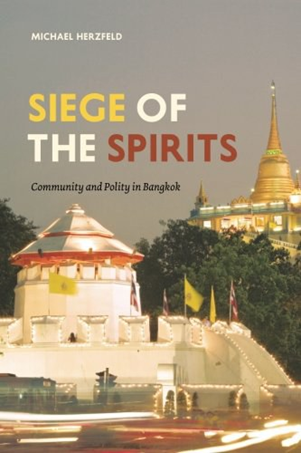
二、人类学参与政治讨论的轨迹
可见,城市空间改造绝非仅仅基于客观事实进行,这其中不可避免地引入了政治性的讨论以及权力的运作。而人类学家在其中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身份?是否应该保持“绝对中立”?Herzfeld通过介绍 Pom Mahakan和Roma的例子,勾勒出了人类学参与政治讨论的关键轨迹。
首先,针对人类学者参与公共政策议题经常面临的挑战——收集的数据样本量小,Herzfeld正面进行了反击,他通过自己在Pom Mahakan的研究论证了小社区研究的价值——即时它只包含10户人家。但样本拥有的代表性意味着很有可能还有更多此类社区正遭受相同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这10户。通过将实地研究范围缩小到这个小社区,他能够更加加强接触私人信息的机会,使他能够从一些经济上最不占优势的居民的角度看待这个Ra城市改造项目,它也是折射整个泰国政治的一个微观棱镜。我们不应该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假设——小社区与人类的未来无关。同时提出的关于官方叙事的问题往往是一个有益的提醒,即人类有不止一种叙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这样的团体就是捍卫人类学学术事业本身。
同时,Herzfeld提出了一种区别于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的参与人类学(engagement anthropology),前者将干预或措施(intervention)视为自己的目标,而后者允许参与(involvement)从学术追求中产生,这既将学者引导到特定的地点或群体,又为信息者面临的困境提供了启发性的见解。这种实用的观点更充分地考虑了伦理复杂性,并要求对之进行仔细评估,反映了社会结构的经验现实总是(而且只是)出现在社会互动的实际表现中——在日常生活和实地研究中——并且通过创造性地发挥其惯例而变得显而易见的方式。Herzfeld提出了对于本质主义(essential relativism)的批判——试图将复杂混合物的整体捕捉为具体化的“文化”或根据固定的道德准则总结适当的反应只会掩盖所有重要的细节。而只有通过这些细节,我们才可以将情况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人类学者采用本质主义(essential relativism)的视角,那么便是应了官僚们的迫切需求——赶紧为这个社区贴上“贫民窟”的标签然后名正言顺地将其清洗。正如Herzfeld在文中描绘的真实场景,官员们可能会将某个社区制造成“毒品泛滥”的假象,然后以此为由拔掉这颗眼中钉。
这种参与人类学(engagement anthropology)接受了这样一种预设,认为社会生活包含在理论与描述、结构与作用、规则与实践的完整且无等级的相互关系中,它们是一组平行的二元序列。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们能够很清晰的讨论学术研究与政治承诺之间的关系。学术研究往往面对的是那些随时发生变化的研究对象,如果学术承诺具有某种“结构”和“惯例”(比如对居民许下的政治承诺),那么它为人类学者日益陷入的斗争提供了框架和可管理性。另一方面,这些斗争以及人类学者的参与都塑造并改变其研究视野,这种直接的经验本身就是实践理论命题的务实证明。也就是说,对于参与人类学(engagement anthropology)来说,结构和实践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
面对政治讨论时常出现的两种不同政治态度时,显然人类学家假装中立无益于解决问题。我们可以为行动者提供广泛的替代选项和概念以便社会行动者能够做出充分知情的选择。此外,选择的存在意味着我们也有机会证明社会伦理的复杂性,同时基于相互宽容和尊重的原则,这种复杂性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许也可以因此对人们的生活结构产生持续影响。我们面前的任务既明确又紧迫。此时人们正被诱人的简单化概念当成靶子,而人类学者的任务便是对这种错误的简化论宣战,要使这种多样性、复杂性能够被公众所接受,并散发其魅力。
推介:欧阳江影
编辑:方志伟
--
参考文献
Michael Herzfeld.2014.Engagement, Gentrification, and the Neoliberal Hijacking of History. Current Anthropology 51:259-267
潘天舒.“文明”“历史遗产”和“士绅化”的人类学批判———以赫兹菲尔德的田野民族志实践为例[J].思想战线,2017(2):15-21
--
推荐阅读:潘天舒 | “文明”“历史遗产”和“士绅化”的人类学批判——以赫兹菲尔德的田野民族志实践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