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2023年5月21日,朱剑峰教授在医学与社会科学工作坊暨医学与社会科学青年沙龙成立仪式上为我们带来了题为“健康的生物医疗化——纪念Sharon Kaufman教授逝世一周年”的讲座。该文是对朱剑峰教授讲座的整理与回顾。
---
谢谢主持人。
我今天想借着这个机会追悼一位我非常尊敬的老师、也是我忘年之交的朋友,著名的医学人类学家 Sharon Kaufman(莎伦·考夫曼)教授。

图一 朱剑峰教授讲座现场
Kaufman教授于 1980 年在UCSF 医学院和UC Berkeley人类学系的开创性项目中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她担任UCSF医学人类学博士项目、医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的主席,同时是健康与衰老研究所(IHA)的一员。
Kaufman教授曾在2014来复旦进行短期的访问讲学,并在2017年9月作为资深复旦学者项目的特邀教授,在复旦大学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进行教学和科研指导工作,她与复旦人类学情谊深厚,亦师亦友。

图二 Kaufman教授曾在复旦大学访学
一、一封邮件
2021年的10月2日,我收到了Kaufman生前最后一封邮件。在这封邮件中,除了她一贯的对于生活的热爱、对研究的激情、对我学术道路的鼓励之外,还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她和她六个月大的孙子,他的名字Lev在希伯来语里是Heart的意思。当时我一时没有回复,她说不用着急,她将和她的先生一起去墨西哥旅游。

图三 Kaufman教授及其孙子
但让我震惊的是,再一次听到她的消息竟然是医学人类学会发的讣告,她已经去世了。这是一封没有办法再回复的信件,是我一生的遗憾。
但我同时又十分欣慰,在And a Time to Die这本书里,Kaufman改变了我们对医院中出现死亡形式——对改变生命结束时采取的措施——的理解。我从美国医学人类学学会的网页上了解到“Kaufman于2022年4月2日星期六在加州的家中去世,她去世时被家人包围,看着她美丽的花园,没有任何痛苦。她享年73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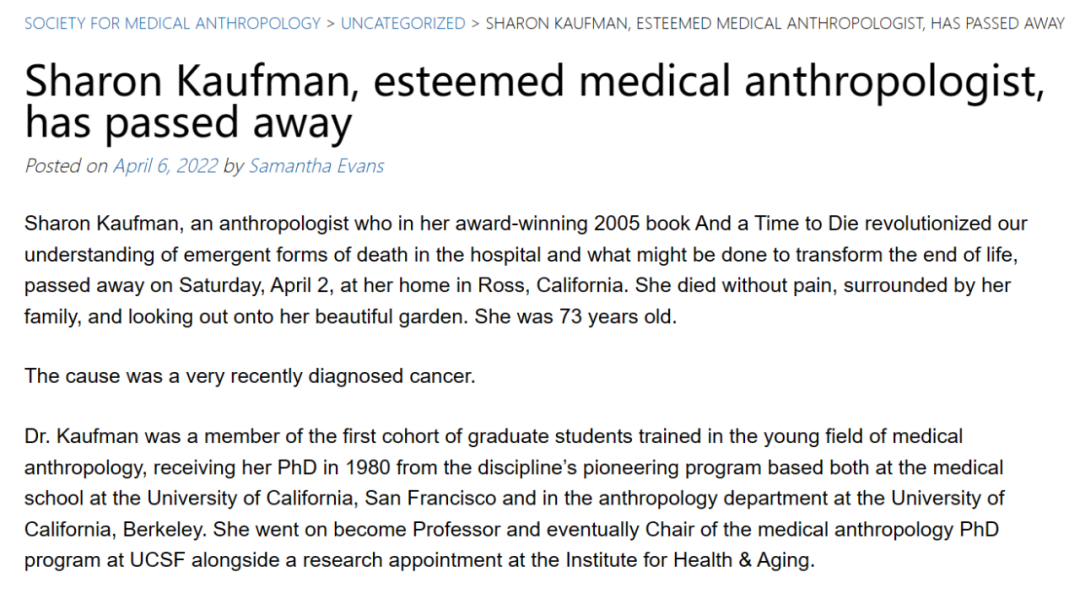
图四 Kaufman教授的讣告
我非常敬佩她,因为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在田野里一直做关于老年课题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临终时的技术研究。最终她也践行了她自己的信念,没有做过多的医疗干预,平静地离开了我们。
二、健康的生物医疗化
我想,缅怀她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她一生的主要观点分享给大家,她的观点一直在激励着我,而且我的研究与她的研究之间有着一些共鸣。
这是她的 4 本书,我不再一一介绍。这是她早年的The Healer's Tale 和 The Ageless Self。当然还有两本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是And A time to Die,还有一个就是 Ordinary Medicine。其中And A time to Die 被翻译成中文叫《生死有时》,由我们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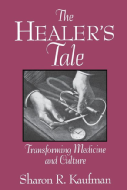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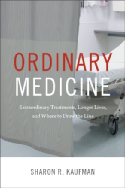
图五 Kaufman教授的四本书
我想她的一生,她的研究的框架实际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医疗化的延展,就是社会医疗化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非常老了,它是社会学家Irving Zola提出的,她认为社会医学已经成为了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的机制,代替了传统的法律和宗教——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维持健康,健康成为了一种美德,那么从而整个社会就走向了医疗化。
所谓的医疗化也就是“ To Make Medical ”。这个进程开始于18至19 对医学职业关注的扩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体现是对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管理。从出生分娩,到新生儿,到婴儿,到青春期,到成年,一直到衰老和死亡,所有的生命阶段都被纳入了医疗化的过程。另外一个体现是通过理性的应用科学来实现标准化的管理。
而这几年一个新兴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城市的中产呈现出一种Desire for medical intervention,这是一种表达我(在医疗过程中)想要被干预而不是不要被干预的欲望。在我们自己的田野里面,包括我在生殖这个领域里面做很多田野里面都看到了这种变化:以前大家不太提干预,到现在,即使是医生再告诉你“你要相信你自己的身体”,她们已经不相信了,就是一遍一遍地(通过医疗干预)测试着自己的身体。
三、医疗干预的“欲望”
我们怎么理解这种欲望?Kaufman在关于衰老的研究中给出了解释,她认为在衰老领域,一旦“通过使用医学干预来延长寿命”这一想法被建构,被表达,甚至被提供给社会,那么它就必然会成为社会伦理观中一个非常正常的部分,此时个人、家庭、社会义务的范围也就被改变了。

图六 朱剑峰教授讲座现场
我们需要对干预本身的正确性、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进行社会科学的审查。Kaufman说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描述在向老年人提供这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发生各种变化,描述她们个人的经历,并且分析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关于老年知识临床干预的这种期望的。
在她长达几十年的田野里,她发现医学对个人晚年生命的医学干预呈指数级的增长,比如支架,比如心脏起搏器,比如肾脏血液的透析,比如肝脏移植……我们已经失去了讨论死亡的空间,不再去思考和讨论一个好的死亡应该是怎么样的。
其实在以前,很多好的死亡是悄悄来临的,是在梦里发生的,而现在当我们,尤其是有心脏病的,对吧?是不允许(其他方式的死亡的)。有了心脏,就要有心脏起搏器,本来已经“过去”了,又把他给唤醒——这是不是我们需要的死亡?延长生命的技术某种程度上就是延长死亡的技术。
在呈指数级增长的医学干预下,我们对衰老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变化了。
首先,衰老是可以逆转的,而且干预导致了更多的干预,对于年龄本身的风险考虑在降低。Kaufman的田野在美国,美国的器官移植手术成普应该最知道了,以前可能 70 岁以上的老人就不再做了,而现在 80 岁和 90 岁的老人仍然在使用这个这项技术——所以对于老年人,年龄本身的风险在逐渐降低,而对于正常的、适当的死亡年龄的理解又在增大,我们不再去讨论什么时候是一个合适的年龄。

图七 讲座现场
四、新的伦理
我记得今年有一位研究生同学做的论文里面就指出,在农村, 70 岁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不停地讨论死亡了,但是我们周围大家都好像是一个Taboo(禁忌),不愿意去提及年龄和死亡的问题。Kaufman教授认为这创造了新的伦理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对于医疗干预说不?
这种新的伦理就呈现出来了三个特点。
1.临床医学为病人、未来的病人、他们的家人和医生提供的关于是否和何时使用延长生命的程序,以及是否和何时停止这些程序的所谓选择,其实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选择。相反,选择权被隐藏在常规治疗中。
2.护理和关爱的性质已经改变,因此护理 (包括医疗和家庭) 、感情和价值的表达与临床行为明确地联系在一起,要么延长晚年的生命,要么允许“放手”
3.作为治疗选择的干预措施引起了对治愈、恢复、提高生活质量的希望和期待反过来,在追求生命最大化的过程中,医学对治愈、增强生命和延长生命的关注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了。
我们看到选择就被掩藏在这些常规的治疗中,当技术在老年的群体中被试用、被证明有效,就变成了常规化,变成了一种routine(日常)。
当临床医生和病人越来越期望干预技术的使用——就是技术放在那里,你用还是不用,就和你是否孝顺联系在一起,当技术变得不具有这种侵入性或者是较低的这种死亡风险的时候,对于技术的需求、道德、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在临床上,对于这些干预的实际选择被取消了。以城市为导向的医疗服务导致了病人、家庭和医疗人员“对治疗干预说不”几乎是不可能的。
照料和关爱的表达与延长生命的唯一的需求捆绑在了一起,医学的技术要求已经成为家庭和临床医生的道德要求。对于病人来说,晚年干预的正常化、接受治疗和保持生命是双重的义务,选择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被家庭的义务所取代了,你没有这个选择。
干预措施的常规化和正常化激发了人们(最大化延长寿命的)希望,(这导致)没有正常的衰老。目前这种老龄的生物医学化趋势否定了自然老龄化和生命终结感的可能性,而且老而不衰。当今生物医学的一个主要的影响是,老年人的身体就往往被视为同时是一个有病的身体,一个被需要修复的地方,是一个需要改进的空间。
所以 Kaufman 教授就提出来了这几个问题,供我们思考未来的照顾是怎样的。
生物医学技术提供了最强大的逻辑,最普遍的方法,以显示我们的关爱。在医疗框架之外,然后在权利和待遇的修辞之外,显示对最年长一代的关怀和爱,是否可能?如果像Rose 和其他人所建议的那样,身体经成为对生命进行伦理判断的最重要的场所之一,那么当一个年老的身体可以明确地从医疗干预中“受益”时,还有什么其他的框架是可能的? 在身体和医疗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方法来证明价值和爱?
这是 Kaufman教授问我们的问题。

图八 Kaufman教授访问期间与陈虹霖教授、朱剑峰教授交谈
五、被神话的技术
生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衰老和生育的话题同等重要。Kaufman教授在最后一段时间给我的几封信中,最大的乐趣就是和我分享自己孙子Lev出生的故事,她鼓励着我继续从事生殖领域中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因为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呼应和对话的领域,在老年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同样存在在生育领域中,这就是生育的医疗化。
我们看到的生育就是这样的(见图九):要在医院进行生产分娩。在这里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看到(生育的)每一步都有医院的干预,一个正常的、自然的分娩早已成为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最终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些医学技术的必要性问题。

图九 医院中生育的画面,截自ppt
在人类学界,我们有一个组合拳的提法,就是One -Two Punch——第一拳是用技术改变自然的过程,这个过程会造成一些问题,第二拳就是用更多的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我们用技术来肢解原本自然的过程,然后用更多的技术再去修复问题的时候,我们实际是相信技术干预会使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更加安全——这是第二拳的重点。
在这里,我引用了Davis-Floyd的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到生育中的医疗化如何对应着衰老领域中的医疗化
“我们的文化将分娩已经置于了风险之中,并将分娩风险的干预变成了一种规范化,对于出生的恐惧同样适用于对于死亡的恐惧,已经成为了美国文化中生育的基础。分娩在文化上已经成为了病态,成为了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同样,衰老和死亡也是)
我想这不仅是美国文化中的基础,也是我们现代产科文化中生育的基础。这是一种被神化的技术和控制的文化,同样适用于衰老和死亡。
产科里面也存在这样的悖论:通过干扰正常的生产生理学努力使生产更安全,但是却造成了分娩者和婴儿的伤害。居高不下的剖腹产率,这里面许多都是没有必要的,不仅不能拯救生命,甚至造成后遗症、感染、失血、血栓和未来的生育问题。所以,顺着Kaufman教授的观点,我也想让大家思考两个问题:
分娩照顾如何以女性为中心并给予新生母亲赋权?
我们是否可以在现行的产科框架下来有分娩照料的多样选择?
最后,我再分享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讲座。我特别清楚记得,当年我在田野里总被医生询问医学人类学的作用,面对医学知识的“权威”代表,我总是惶恐不安,不知道怎么回答好。Sharon坚定地看着我说,她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面对这样的质疑,她要我骄傲地回答,“医学院学生培养8 年,我们人类学研究生到博士毕业也要至少8年时间。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研究,深刻地揭示医学的文化,医学技术里面的弊端,我们当然能够用我们的知识帮助产生更好的医学。”
希望我们医学人类学学者能够更加有勇气、底气和骨气,参与到与我们健康福祉息息相关的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用我们的研究去启发大家思考有关生命的永恒命题。
今天,我仅用这个简单的讲座来寄托我对Kaufman教授的哀思。这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医学人类学家Pricilla Song在Sharon去世后代表我们制作的一张照片剪辑,在这里我展示给大家。

图十 来自中国北京、上海、香港医学人类学界的朋友们与Kaufman教授的合照
注:感谢潘天舒教授、朱剑峰教授供图
往期回顾:纪念莎伦 · 考夫曼(一)| 复旦人类学的导师、同事和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