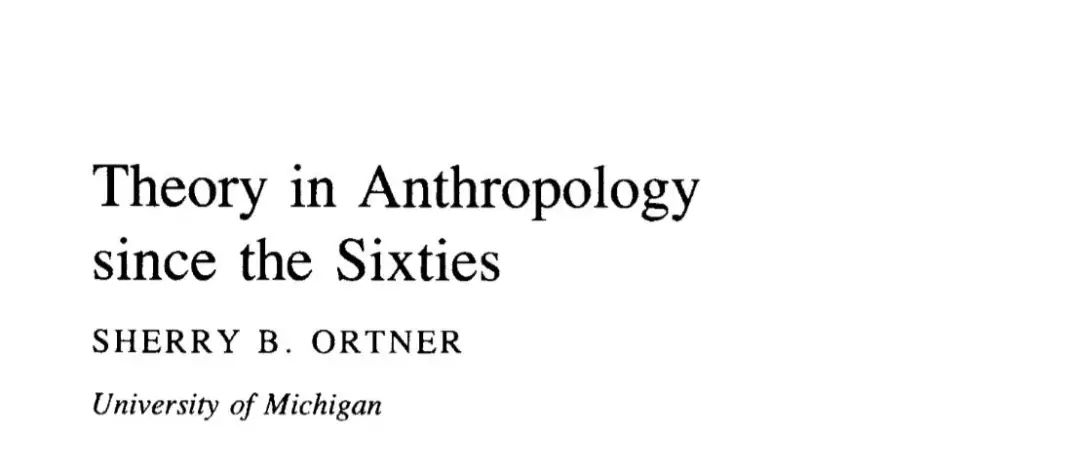
每年在美国人类学协会(AAA)召开会议时,纽约时报都会要求一名大牌人类学家贡献一个关于学科发展形势的专栏。这些专栏都倾向于采取一种相当悲观的观点。比如说,几年前,马文·哈里斯(Malvin Harris)就暗示说人类学已经被神话、宗教信徒和加利福尼亚的宗教信仰给接管了。那个会议被萨满主义(shamanism)、巫术和“不正常现象”的专家组主导了;然而,“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科学论文”被自愿地排除出了项目(Harris 1978)。更近一些,用一种克制的语调,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人类学领域正在分崩离析。次级领域(次次级领域)正在逐渐发展它们的专业兴趣,领域之间和整体学科逐渐丧失了联系。学科不再有一个统一的话语体系,不再有一系列共享的可供实践者定位自身的术语体系,也不再有独特地所有人都共享的语言。(Wolf 1980)
学科的现状的确像沃尔夫所说的,学科领域逐渐破碎与分割化,个体们和小集团从事着彼此分割的调查,且只与他们自己对话。我们甚至再也听不到刺耳的争论。虽然人类学从来没有在事实上采用过共享的单一范式,但是至少仍然有一段时间学科有着共享的一些隶属理论范围,一系列可辨明的阵营和学派和一些简单的可以向反对者大声说出的表述词。现在,甚至这个层面上的精神也显得冷淡了。我们不再叫彼此的名字,不再确定界限如何划分以及应该把自己置于何处。
作为人类学家我们能够辨认出我们正处于阈限的经典征兆中,充满了对范畴的迷惑与混乱无结构的表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无序也许就是更好秩序的温床。的确,如果更仔细地观察,我们也许能够分辨出即将到来的新秩序的大致形状。这就是我在这篇文章当中想要做的,我将表明一种新形式的理论取向的核心象征正在诞生,它可以被标示为“实践”(practice,或action、praxis)。这既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也不是单一的方法,而是一种象征,以之为名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将会被发展起来。为了去了解这种趋势的意义,我们必须倒退20年看看我们从何处开始,以及我们如何走到今天。
在我开始这项工作之前,辨明它的本质非常重要。这篇论文将会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关注各个理论流派和发展路径。所有的流派都不会被全面概括和单独讨论,相反,我会标明一些与主流趋势相关的理论主题和层面。每个人类学家可能都会发现他(她)喜爱的学派被过度简化。如果不是完全曲解,在某种范围内,我也会选取强调与实践者通常采用的角度不同的特定的角度作为其最重要的理论特点。因此,如果阅读者想要从内部探讨的特定理论范式,那么他们应该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这里的关注点主要是阐明各个理论的关系。
六十年代:象征、自然和结构
虽然选择一个起点对于历史探讨来说总是相对武断,我还是决定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一方面,那是我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同时由于我总是认定追求某种系统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至少从行动者的角度来说,我也从起初就开始糅合理论和实践。因此,可以确认的是这个讨论并不是来源于表面的假设性观点,而是来自于经由60年代至今的人类学中特定参与者的行动视角。
但是参与者总是希望去声明其经验和阐释的普适性。我将会进一步说明,从相对客观的视角上说,自60年代以来人类学理论就有一股主要的革命性力量。实际上,修正主义混乱(revisionistupheaval)也是那个年代其他领域的特征。例如,在文学批评领域: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一种(涉及)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符号学(semiotics)、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接受美学(receptionaesthetic)的变化无常的混合物开始去取代早先的道德人文主义(moral humanism)。文学文本开始趋向于这样一种现象的地位:一种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语言的和意识形态的事件,它来自于被给予的语言的竞争、可用的叙述顺序的分类学、题材的排列、结构化格式的社会学选择以及宏观结构的意识形态约束。这时存在着一种广泛的、有争议的修正主义观点。
50年代末期的人类学,理论手艺人的工具箱里主要包含三种主要、讨论透彻的理论范式——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继承自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美国的文化和文化心理学人类学(继承自玛格丽特·米德和露丝·本尼迪克特)和美国进化论人类学(以莱斯利·怀特和朱利安·斯图亚特为中心,与考古学有很强的隶属关系)。同时,在50年代处于我们关注中心的参与者和学者也在这些领域内接受训练。他们在60年代初开始崭露头角,并且提出一些关于如何去加强他们导师和祖先的范式的激烈观点,以及对于其他学派的竞争性态度。正是新观点的综合和知识分子的竞争性引起了三个方面的运动:象征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文化生态学(culturalecology)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象征人类学
“象征人类学”是其主要倡导者在其形成期从未使用过的标签,。不如说它是一个简短的标签,一系列更加分化的趋势的保护伞。两个主要的支流被独立的发明,一支来自于芝加哥大学的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和他的同事,另一支来自康奈尔大学的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格尔茨派和特纳派的不同很难被象征人类学领域以外的人察觉到。然而,格尔茨派首先是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影响(经由帕森斯),而特纳派则是受到涂尔干的影响。格尔茨派主要代表了早期美国人类学对“文化”看法的变化,特纳派则是代表早期英国人类学对“社会”的看法的变化。
格尔茨最激进的理论进路就是认为文化不是“锁在人脑内的某种东西”,而是嵌入在公共象征符号里,经由这些象征符号,社会成员能够与其他人、后代以及人类学家交流他们的世界观、价值取向和道德观。经由这样一种构想,格尔茨了迄今为止含糊不清的文化一个相对固定的轨迹和一定的客观性。关注象征符号为格尔茨和其他人带来了启发式的解放:告诉他们到哪里去寻找他们想要研究的东西。同时,象征符号是表达意义的终极手段,对象征符号的研究并没有局限在他自身。因此,格尔茨派从没有对区分和范畴话象征符号类型(信号、标识、肖像、指标等等)产生兴趣,也没有对象征符号在特定的社会过程中发起实践性行动产生兴趣(正如特纳),这些实践性行动包括治疗仪式、过渡仪式、通过巫术来杀人等等。格尔茨派并没有忽视这些实践性的社会影响,但这些象征符号并不是其核心关注点。相形之下,格尔茨派人类学持续关注的问题是象征符号如何塑形社会参与者看待、感受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象征符号如何作为表达意义的手段而发挥作用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预料到与结构主义的讨论,格尔茨的核心更加关注的是文化的“气质”(ethos)而不是“世界观”(worldview),更加关注情感和风格层面而不是认知层面。虽然很难完全区分二者,然而的确存在对一遍的侧重。对于格尔茨来说(尤其对于在他之前的本尼迪克特),即使是最体现认知和智力的文化系统,比如说巴厘人的日历,也不单单会被简化为一系列的认知指导原则,而是去理解巴厘人时间的分割方式如何给他们的自我意识、社会关系和行为铭刻上特定文化差异的特点和气质。(1973e)[1]
格尔茨的框架的另一个贡献是它对“从参与者观点”研究文化的坚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跑到“当地人的脑子里”去。简而言之,它意味着文化是行动者试图去为他们生存的世界赋予意义的产物,如果我们想要去掌握一种文化的意义,我们就要进入到文化被建构的地方。文化并不是从隐藏的结构性原则汲取逻辑的抽象组织系统,或者从特殊的象征符号中汲取整合性因素。这种文化的逻辑来源于组织性系统和抽象逻辑,来源于在特定组织化秩序中行动的人,这些人定位着自己的位置以便更好地和组织协调。在这里需要指出,虽然参与者中心对于格尔茨的理论来说处于基础性地位,但是并没有得到系统地阐明,也没有建立一套参与者和实践的理论。不过,他的确将参与者放到这个理论的中心位置,很多的实践中心的作品都建立在他的基础之上。
另一个芝加哥学派象征人类学的主要任务是大卫·施耐德(David Schneider)。施耐德和格尔茨一样是帕森斯的学生,他也将注意力放在文化概念的改进上。他努力通过“核心象征”(core symbol)和一些与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相似的理念去理解意义和象征系统的内在逻辑。(1968,1977)事实上,虽然格尔茨第一次使用了“文化系统”这个术语,但他并没有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文化的系统性层面上,施耐德在他的作品中则将文化从社会行动中区分出来,这相比起格尔茨更加激进。同时,也许由于社会行动(或者说实践)在施耐德的作品中被如此激进地从文化中分割出来,他和他的学生成为了成为了象征人类学中最先将实践看做一个问题的人(Barnett 1977,Dolgin,Kemnitzer,and Schneider 1977)。
维克托·特纳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知识背景。他在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一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构功能主义接受学术训练,强调正常的社会形态并非同一性和各个部分的和谐统一体,而是充满的冲突和矛盾的。因此,分析性问题并非团结性是如何保持一致、加固以及加强的,这样直接继承自涂尔干的问题意识,而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常态的冲突与矛盾中如何建立和维持社会团结。对于美国读者,这对于功能主义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变量,因为对于这个学派来说重点依然是对整合的维持和“社会”——参与者、群体和社会整体,的整合与加强,而不是“文化”。但是格拉克曼和他的学生(包括特纳)相信他们与主流范式之间有很深的不同。同时,他们也总是英国学界的少数分子。这个背景可能也导致特纳相对于同胞,有着很强的原创性,最终导致了他独立地发明了一个细致的象征人类学。
虽然特纳关注象征符号有着相对新意,然而,在他的作品中仍然对英国人类学的关注点有所延续,因此与格尔茨的象征人类学有很大的不同。对于特纳来说,象征不是对于“文化”的分析性窗口的通道——一个统和性社会的气质和世界观,而是社会过程中的行动者们(operators)在被置入一定的特定社会背景的社会安排(尤其是仪式)之后能够制造必要地社会变迁。因此,恩丹布人(Ndembu)人在治疗、入会或者追猎仪式中的象征符号被调研为将参与者从一种地位转移到另一种,消解社会矛盾和将参与者融汇到社会的范畴和规范当中(1967)。沿着这些更传统的结构功能目标,特纳辨识和阐明了一定的仪式动力学,同时他使用的一些概念成为了仪式分析中不可取代的部分—阈限(liminality)、边缘(marginality)、反结构(antistructure)、共态(communitas)等等(1967,1969)[2]
特纳和芝加哥学派的象征人类学学派并没有与彼此产生冲突,而是相互补充。然而,特纳学派补充了一个重要而且具有英国特点的层面到整个象征人类学领域,一种“务实”的象征符号。相比起格尔茨和施耐德,他们调查更加注重细节,以及“符号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 of symbols)——象征符号如何按照人类学家们声称的方式发挥作用的问题——在社会过程中发挥一个积极的能动者作用。(Levi-Strauss 1963,Tambiah 1968, Lewis 1977, Fernandez 1974)
事后看来,也许会发现象征人类学有一些很重要的缺陷。我并不想像文化生态学者一样将之批评为不科学的、神话的、文学化的和愚蠢的;我宁愿指出尤其是美国形式的象征主义人类学缺乏一种体系化的社会学;缺乏对文化的政治方面的认识;缺乏对象征系统的产物和维持的兴趣。这些都将在这篇文章的下面有所讨论。
文化生态学
文化生态学代表和发展了一个对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1943 1949)、朱利安·斯图亚特(Julian Steward)和高登·凯尔德(Gordon Childe)的物质主义进化论理论的新综合。它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和泰勒(E. B. Tylor),最终回归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50年代的进化论者由于政治原因没有标明自己与马克思的关联。
怀特一直致力于针对社会复杂性和科技进步的阶段的“普遍进化论”(general evolution)或者说普遍的文化进化论。这些阶段进一步被塞维斯(ElmanService)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该进成著名的Bands-Tribes-Chiefdoms-States模型。怀特理论中的进化动力学来自于或多或少偶然的事件,导致更强的能量开发能力的科技发明和促使社会政治组织和协调更加复杂的人口增长(或者是战争与征服)。斯图亚特则批判了普遍的文化进化(相对于特殊文化)和缺乏更加系统运作的进化机制。相反,他强调特定文化在适应特定环境的过程中进化出他们独特的文化形式,明显一致的进化阶段只是因为这些世界各地的文化都适应相似的自然条件。
如果关于文化嵌入在公共可见的符号中将象征人类学从早期的美国文化人类学中解放的话,那么“适应”(adaptation)的观点就在文化生态学中发挥着相似的作用(Alland 1975)。正如格尔茨宣扬“文化嵌入在符号当中”的观点取代“文化是人脑内部”的观点一样,萨林斯宣扬将对环境的适应是文化的格式塔(cultural gestalten)和历史辩证法(1964)。对美国的“文化”和英国的“社会”这样的内部研究有大范围的排斥。内在的动力学很难被测量,很难去赋予其因素以因果上的首要性,然而外在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则是可验证的独立变量。
这个世纪的数十年,知识分子之间一直就什么是文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而争论。很多人进入了不同的口号当中,有趣的是,很少有人真正落到实处。莱斯利·怀特将科技进步当做文化进化的首要因素,朱利安·哈克利和其他一些人认为“人的责任感”是决定性力量,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也是争论的焦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是这些观点都认为发展的动力是从内在产生的。当指向机制时,发展的内在原因被增强了,比如黑格尔的辩证法,然而它也许是建立在对逻辑的不稳固观点之上的。大多数情况下,总有一个假设在那里,那就是文化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这个观点上看,文化生态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讲注意力转移到内在和外在的关系互动上去,将文化和环境的交互改变当做进步运动的主要动力。现在很难从一篇文章上看出那个观点将会更加普及,但是如果“适应”战胜了“内在机制”,那将会有本质和明显的优势——因为适应是真的和自然主义的,深深地固定在文化的历史背景中,这一点是内在机制所忽视的。(Sahlins,1964)[3]
萨林斯和塞维斯对于文化生态学的说法符合考古学的主流,从基础上是进化论主义的。适应主要用于对社会形势的发展、维持和变迁的解释中。但是还有另一支相对较晚的文化生态学决定了60年代的物质主义分支。它的立场被马文哈里斯(Malvin Harris)最有力地论述,拉普帕波特(Roy Rappaport)最优雅地论述,将重点放在了系统理论上。它将注意力从进化上转移到对特定文化中存在的特定段落的适应性和结构维持性功能的讨论中去。因此,Maring的Kaiko仪式防止了自然环境的恶化(Rappaport 1967),Kwakiuutl的夸富宴在部落间维持了食物的分配的平衡(Piddocke 1969),印度牛的神圣化维持了其在农业食物链中的核心纽带作用(Harris 1969)。在这些研究中,兴趣从环境如何影响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发展转移到社会和文化形式如何维持与环境的关系中发挥功能。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当时中文化生态主义者和象征主义人类学家之间的激烈争论,那么他一定是人类学理论的外行。文化生态学家认为象征主义人类学者是疯狂的唯意志主义,总是沉浸于不科学和无法证实的主体阐释中,象征主义人类学者则认为另一方沉浸于无聊贫瘠的科学主义中,计算着卡路里和瀑布流量,自动地忽略人类学的真理:文化调节着人类行为。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硬理论和软理论,阐释性的内在视角(emics)和解释性的外在视角(etics)主导着60年代大部分的时间,以及70年代的一些领域。
我大多数人的思想和作品都面临着来源于西方思想普遍存在理论图示的矛盾:主观和客观、自然和文化、思想和身体等等。田野调查中的实践也许会进一步导致这样的想法,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指令之上、一次只能关注一方面的参与和观察。这种知识领域上的极端化建构被文化范畴和实践形式所鼓励的程度太深以至于很难去消除。但是60年代的内在和外在视角之间的争论也导致了一些不幸的后果,至少阵营两方都缺乏对自身足够的反思。事实上,两方都都沉溺于批评对方的错误,而没有审视自身的局限性。事实上,两房都不仅仅没有把握住另一方所做的(象征主义完全与“解释”(explaining)断绝关系,文化生态学完全忽视了人类行为中的意义),而且两方都缺乏了系统化社会学的思考。
事实上,对于英国社会人类学来说,整个美国的斗争都很没有意义,因为它们都遗失了整个人类学讨论的必要术语——社会。社会群体、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这些不仅调节着人类所想(文化)也调节着人类如何体验以及行动于环境的因素在哪里呢?但是这一系列的问题很难用英国的社会人类学范畴来回答(也没有人去询问),因为英国人也在经历着他们自己的知识混乱,这是我们接下来的议题。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列维斯特劳斯一手创造出来的,也是在60年代唯一的新范式。有人甚至会说,这是20世纪唯一的社会科学(对于人文学科也是)新范式。借鉴了语言学和沟通理论,以及自认为受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通过证明这些现象中共享的关系都与潜在的规则相符合,令人迷惑的社会与文化现象将会变得可知。他开始去建立关于普适性的文化话语的单元在其中得以构建(经由二元对立的原则)文化语法,以及被人类家记录下来的原则,经由这些原则,一系列的单元被安排和组合去造就现实的文化产品(神话、婚姻规则、图腾的部落安排等等)。文化首先是一系列的分类体系,以及一系列建立在分类体系上并反作用于分类体系的组织和智慧产物。文化相关于其分类学最重要的次级作用就是去调节这些分类学之间的对立。
在实践中,结构分析由一系列经过筛选的暗含在复杂文化现象(神话、仪式、婚姻体系)之下的对立组成。结构分析也包括反映现象是对立和对立再生产的表示,因此创造了一种对秩序的文化表述和反映。甚至没有对文化和仪式进行完整分析,对一个文化中的重要对立面进行单纯的列举也是一项有意义的事业,即使不彻底分析某一神话或仪式,单纯列举其中的对立面也是很有意思的工作,可以显示某一特定文化的思想深度,也可以想象相关文化的某些思想局限(Needham 1973b)。然而,对结构分析最完整的证明还是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四卷本《神话学》(Mythologiques 1964-71)。在那里这种方法不仅建立在大范围之上(包括了南美本土和部分北美),也建立在对无数小细节的解释之上——为什么美洲虎会在笑的时候捂住嘴,为什么蜜蜂隐喻描述了游戏动物的逃离。是广泛和细微细节的组合给了这些作品以巨大的力量。
关于列维斯特劳斯最终将他从社会和文化中识别出的结构归之于心智的结构有很多的观点。无论是这个观点自身,还是对它的批评看似都与人类学家无关。所有人类和文化都会分类是无可争议的。这暗示了先天的心智倾向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特定的分类图示都是必然的,食欲是必然的,作为分类体系的食谱则是偶然的。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持久贡献就是丰富的多样性甚至表面上的偶然性都有一个更深的来自一些潜在的规则的统一性和系统性。正是在这样的方面,列维斯特劳斯声称它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也强调在形式表面扩散的之下有着相对简单和统一的动力机制在运作着。(DeGeorge and DeGeorge 1972)这样的观念也让我们将简单的变迁与真实的变迁(进化)区分开,简单的变迁总是在一个给定的结构中运作,而真实的变迁则是结构本身的转变。因此,尽管结构主义有自然主义和生物主义的基础,尽管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偏向于考虑“越是改变越是一样的结果”(Plus ca Change,Plus c‘est la meme chose),这个理论相比于大师的实践带有更多的历史和进化的人类学。路易斯·杜蒙特(Louis Dumont)发展了一整套对印度种姓制度结构分析的进化推论,说明了从种姓到阶级变迁中深刻的结构性转变。(1965,1970;也可见于Goldman1970, Barnett 1977,Sahlins 1981)[4]
结构主义在美国人类学家中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受到欢迎。虽然它一开始(更多地被文化生态学家)被看做是象征主义人类学的变体,但是它的核心假设却与之有很大的不同(对施耐德有部分例外)。概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1)列维斯特劳斯对意义的纯认知的强调与美国人对气质和价值观的兴趣完全不同。(2)列维斯特劳斯对符号任意性(arbitrariness of meaning)的严格强调(所有的意义都是建立在对立基础之上,意义并不附带在任何事物身上)与美国对象征符号的形式建构和其携带的内容之间关系的兴趣完全不同。[5]从参与者的行动和意向中分离出的明确抽象的核心结构也与象征主义一贯的行动中心(actor-centrism)完全不同。从这些原因上看,结构主义并没有像表面上认为的那样被象征人类学所接纳。它们被赋予了虚构的亲密性也许只是因为它们都关注相似的领域——神话、仪式、礼仪等等。
结构主义在法国以外的主要影响就是在英国,主要对一些富于冒险精神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Leach 1966)。列维斯特劳斯和英国人事实上与对方非常亲密,都是承袭自埃米尔·涂尔干。结构主义在英国背景中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否定了心智的问题和普遍的结构,英国人类学家将结构分析应用到特定的社会与宇宙学中(e.g. Leach 1966,1969; Needham 1973a;Yalman 1969;也应用到法国的Dumont)。他们也更加注重对于对立的调和过程,并创造了一系列对反常和反结构的原创再思考,尤其是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也可见于Turner 1967,1969;Leach 1964;Tambiah1969)
然而,英国的结构主义也有一些激进的特点,它们否认了涂尔干对社会基础(Social “base”)和文化反映(cultural“reflection”)的区分。列维斯特劳斯声称:如果神话结构和社会结构相平行,并不是因为神话反映着社会,而是社会和神话共享着一套相同的结构。很多英国人类学家(Rodney Needham是个例外)则回溯到涂尔干和莫斯的传统中,认为神话和仪式作为象征层面上的对立都被基础社会性所反映和决定。[6]因此,只要英国人类学家把结构主义者局限于神话和仪式的研究,那么在结构主义融入英国人类学的传统理论时,就不会对后者造成颠覆。变成了它们的文化和象征人类学版本,它们的宏大超结构。最后,结构主义的传播预示着新变体即将出现,那就是文化性或象征人类学的视角、新的上层建筑理论。几年后,当系统或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社会结构”这个英国学派的概念碰撞时,立刻迸出了思想火花。
在70年代早期,很多领域——语言学、哲学和历史学都产生了对结构主义的回应。对意向性主体在文化和社会过程中的相关性的否定和对特定历史和事件能够对结构影响的否定这两点受到了广泛质疑。学者们开始去寻找替代性的理论模型,在其中,能动者和事件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些理论模型指导70年代末期才开始在人类学界崭露头角。在70年代的人类学领域,带着所有优点和缺点的(传统)结构主义成为了占统治力的结构化马克思主义(Structural Marxism)的基础。
[1]如果文化本身是一个含糊不清的现象,格尔茨可能探索了它最含糊不清的部分——气质。这也可能对他产生了持续和广泛的吸引力。也许对于大多数学生和大多数被人类学领域吸引的非人类学家,都是被一些异文化的“他者”体验也可以说是气质给深深吸引。格尔茨的作品提供了少数几个把握他者的抓手。
[2]特纳与格尔兹的另一个区别在于:特纳的“意义”概念,在其方法建立之初,只是作为参考,他认为意义是象征符号所指或引申出来的事物,如“母系”、“血统”等;格尔兹把 “意义”定义为事物的目的、用处或重要性,他关注这些问题,曾援引莎翁戏剧《麦克白》的人物弗莱的话:“你无法从《麦克白》中了解苏格兰的历史,只能从中领悟到某人成为国王后,失去灵魂的感受”(1973f:450)。
[3]这是一个纲领性的立场,在实践中,萨林斯也关注了内在的社会机制。
[4]杜蒙特是这些人物中能够得到更多空间去认真阐述的人。
[5]这并不是说美国的象征主义人类学否定符号任意性的信条,但是他们的确坚持认为从一堆可能的同意义象征中选取特定象征不单单不是任意的,还有很多可能结果需要去调查。
[6]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从《阿斯蒂瓦尔的神话》中涂尔干和莫斯的立场转向了在《神话学》中更加激进的结构主义立场。毫无疑问,利奇则选择将《阿斯蒂瓦尔的神话》作为《图腾和神话的结构分析》的开篇论文
本文译者为北京师范大学 吴燕位
转载自公众账号:谦逊的Charisma
联系我们
复旦人类学之友读者邮箱
fudananthro@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