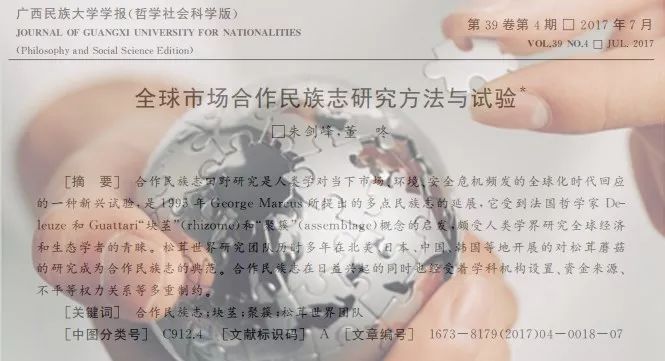
本文发表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4期,2017年7月
[摘 要] 合作民族志田野研究是人类学对当下市场、环境、安全危机频发的全球化时代回应的一种新兴试验,是1995年 GeorgeMarcus所提出的多点民族志的延展,它受到法国哲学家 De-leuze和Guattari“块茎”(rhizome)和“聚簇”(assemblage)概念的启发,颇受人类学界研究全球经济和生态学者的青睐。松茸世界研究团队历时多年在北美、日本、中国、韩国等地开展的对松茸蘑菇的研究成为合作民族志的典范。合作民族志在日益兴起的同时也经受着学科机构设置、资金来源、不平等权力关系等多重制约。
[关键词] 合作民族志;块茎;聚簇;松茸世界团队
市场、国家、生产者、消费者、营销者界限的进一步融合,全球化经济对地域界限的进一步消融,给作为人类学生存之本的民族志田野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从乔治·马库斯GeorgeMarcus1995年提出多点民族志至今,无数人类学者都在对新型民族志和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角色进行新的探索。
与此同时,随着新自由经济所呈现的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出现,比如2008年美国和2011年日本的金融危机,人类学家也不断以文化顾问的新兴职业者身份,加入对市场中“文化”问题的诠释中。越来越多的市场调研咨询公司表现出与人类学家进行项目合作和开展合作研究的意向。作为文化批判者的人类学家不断介入技术、环境、经济、市场领域,并正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合作者,而非以前的简单的参与观察者。
本文借鉴当今人类学界对合作研究的学术讨论,对合作研究方法的缘起、哲学基础、民族志实践及其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合作民族志的缘起
合作,作为一个社会概念,并非不言自明,它在不同的具体情景中被不断地建构、演化,并通过不同的形式被不同的主体实践着。合作要求将处于不同集合和层次相互联系的行动者不断地聚合起来。近年来,人类学文献中使用“合作”概念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合作,这是民族志的传统,合作标志着对主体间性的公开承认和强调。[1]
二是研究者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合作,多见于医学人类学领域,是20世纪90年代后对科学技术的关注的产物,医学人类学季刊中存在大量的公共卫生临床医学专家和人类学家共同署名的作品,在实践中合作研究的课题也多为“合作项目”,人类学家在这种合作研究中的定位具有双重身份,即应用和文化批判。
三是人类学家和人类学家或者与相关社会科学和人文批判研究领域学者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形式尚处试验阶段,但是相对于前两个层次的合作,这种合作更具有创新性,因为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扩张,这种合作在扩大认知的深度上更有优势,也是本文关注的对象。
有学者认为合作研究也是适应目前所谓 “合作经济 ”[2]———“更倾向于使用而不是拥有 ”的经济形式———需要、应运而生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强调的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他者”进行工作的理念,也是一种新兴的“制度和思考模式”。合作(colaboration)和协调(coordination)不同,它倡导的不是专业化的划分、各司其职的集体劳动,而是一种融合一体的互动发展。自然科学、医学等所谓“硬科学”领域中的合作事实上应该是一种协调,因为它们的模式是基于揭示事物客观真相的共同目的,新的方法和新的角度几乎不会改变研究的目的和研究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在这些大的前提下进行专业分工合作并协调方法,因为“真相”的多面性要求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但是大的 “客观性”是不变的。这种合作前提也是很多市场、经济、金融研究的假设。但是,这种分工合作的协调和本文所述的合作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强调的不是专业划分,而是去专业化,研究目的也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揭示和理性的解释和推测,而是一种实践上的摸索。这种去专业化、质疑理性的趋势是由于新自由经济包括环境和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众失去了对专家的信仰所致,比如大数据的兴起,即穷尽一切可能的工具搜集市场上能够搜集到的信息,但不做分类、取样、模拟、模型,也是一种对以往专业分工和专家研究假设能力失去信心的反映。[3]
虽然现在合作正在成为诸多研究领域打破学科界限的方兴未艾的方法,但它在各个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中合法性的取得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仍然在进行中。人类学也不例外。和科学界不同,人类学界一直以个体的智力劳动作为衡量一个研究者的标准,对个人田野经历,民族志专著和单独作者有着恋物般的倾向。尤其是将田野研究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论述的时候,很多传统学者仍然坚信“研究者本人就是研究工具”。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解释框架,因此很难实现合作。比如格尔兹生前就拒绝以合作的形式担当一些学科发展的责任,从现在看来应该是一种损失,因为“系统性地拒绝种种责任和社会关系,尽管可能让人无债一身轻,但是正如布迪厄所将自己从交换的圈中排除出去,而在交换的圈内,社会关系正是通过礼物给予和还礼的不断推迟,并从不终止这样的循环而得以加强和巩固的”。[4](P52)所以无债的状态并非理想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合作的“债”是人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乔治 ·马库斯(GeorgeMarcus)所述“合作一直以来都是个体田野项目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但是合作从来也没有被认为是人类学整体文化方法的显著方面和标准规则。比如,判断一个田野工作者的工作质量,人类学从来不会看他的合作的质量和他对合作的管理能力”。[5](P29)但是,今天,各种形式的合作已经迅速成为田野工作的中介和目标。
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潜在生命力是它本身的研究场域,在人类学中,文化即是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对话者之间的互动产物。斯特拉森(Strathern)指出,人类学学科的重大贡献就是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转化成为一种分析关系。[6]人类学对主体间性的强调也是合作的认识论基础。从根本上看,人类学所有生产出来的知识都是和它的研究对象合作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也最具 “反权威性”。纵观现代人类学发展历史,批判民族志权威作品伴随着学科的发展屡见不鲜,并成为学科发展的动力之一。对于人类学而言,合作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和形式,从方法论和认知论层面上看,它是学科知识的立足点。因此人类学的民族志田野研究是迄今对研究问题最为开放和灵活的一个学科,它对田野中的相遇和互动秉承尊重的态度。笔者在本文中所讨论的合作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求同存异的参与形式,也不仅仅是各方提供各自“专家知识”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平台,更不是以往批判人类学家惯常用以搜集文化批判的附属项目。合作是一个跨界的平台,是正在进行中的一种理论搭建,来自不同领域的 “专家”对自己“专家知识”的一种反思平台,这种合作应该是带有浓重“去专业化”的自反性。人类学家应该在这个合作所搭建的田野中,重新思考,批判以往自己赖以为生的民族志研究工具,探索更多可能,消融历史形成的某种分割。从20世纪90年代“写文化”争论以来,人类学家开始各种民族志研究和写作实践的试验。大家积极尝试参与了包括信息工程、生命伦理、生物医学技术以及艺术设计等不同领域的合作,尽管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这种对他者的融合,以及对自我的反思正是人类学特有的开放气质。
二、合作民族志的理论基础与试验
1995年乔治·马库斯(GeorgeMarcus)首次提出了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ethnography)的概念,用以回应全球化人、物、技术、意识形态跨国界流动对传统单点民族志的挑战。[7]对流动的人员、事物和概念的追踪,将涉及的多个地点连接起来进行参与和观察,重新审视了传统“本地”和“全球”“生活世界”和“外部系统”等二元划分的概念。近年来,对跨国市场,世界系统和移民的多点民族志研究更是硕果累累。但是,多点民族志在实践中却面临着种种实施的困境。比如对研究者每个点的时间分配问题,因为在一定时期内完成多点的田野工作,研究者不可能在一个点上长期浸入,在不同的田野疲于奔波,必然会在深度了解当地人和他们的社会关系上大打折扣。尤其是研究国际市场,涉及生产、运输、销售、市场、调研、组织管理、咨询、品牌推广,以及消费者等方方面面,要初步了解已经高度专业化的各种领域的知识体系,掌握与自己报道人的语言交流,在短时间内几无可能。也正是由于田野工作实施的困难和写作对“流动性”的表现形式的要求,使得高质量的多点民族志凤毛麟角,或沦为简单的几个田野点浅描的累加,牺牲应有的深度,或仅仅以 “多点”的名义从事着单点的工作。 多点民族志对全球市场,跨界流通的研究优势不言自明,但是“孤独的田野工作者”人手精力不足的问题如何解决?人类学家一定要通过“独唱”的形式才能维系自己的权威体系吗?正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经济学界的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对专家体系理性思维的反思相同,人类学家也开始尝试扩展自己的研究工具,试验合作研究的可能。在这些试验的过程中,人类学家汲取了当代哲学领域的发展,丰富了自己的理论工具和学科认知。块茎和聚簇的概念就是合作民族志的重要理论基础。
块茎(rhizome)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在他们合著的书《千高原》A ThousandPlateaus中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8]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比喻,用来改变过去的认知体系中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比如主体客体、原版拷贝、事实解释、主观客观等等。过去的认知体系是以树作为隐喻的,讲究源起,线性发展,而“rhizome”的提出是革命性地动摇了这种认知方式,他们希望为多样性提供哲学想象空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rhizome”这一类块茎植物,比如人参、生姜,是没有垂直的高下等级的,它是水平方向上的链接,无根无茎,无枝无叶,无始无终,从而 “无机”“无极”“无迹”。这样的一种文化模式,从开始就反对“组织性的结构”,反对追求“本源的根”或者是“不加反思的所谓事实存在”,永远都是正在“生成中”,而不是“本体的存在”。除此,Deleuze和Guattari还借鉴了生物学的互惠共生论,用兰花和黄蜂为例说明不同种的生物之间的接触产生出的多样性。生物界中存在兰花和黄蜂直接互相生成的现象,即兰花可以释放出“非兰花”,被黄蜂当作雌蜂进行繁殖,同时黄蜂也被兰花当作生殖器官的一部分加以利用。这“是一种正在生成兰花中的黄蜂和正在生成黄蜂中的兰花”。[8](P10) 它们互相生成,结成“块茎”。这是两个异质元素共生并双向生成的一个例子。当然我们可以去探究其更深层的哲学意义,不过对笔者而言,这是一个描述合作关系的恰当比喻。合作中异质元素———不同学科,不同目的,不同工具———都处于生成中,比如生成中的田野,生成中的文化,生成中的人类学家。Deleuze和Guattari将rhizome作为一种诗学而不是概念来理解:“一种多样性本体论的诗学”它提供的是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本体论的可能,rhizome强调连接,异质性,多样性,而且赋予空隙积极的意义。而且块茎植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使把它砍断了,它也会生长,而且看不出被砍的痕迹,有生成的轨迹,但又无法预测生成的结果,因此永远都是 “生成中”的。这些特点恰恰适应了开展合作研究全球化市场的需要。融合但又独立发展,相互生成但又保持异质,碰撞但不冲突,交汇处即是 “块茎”。合作各方保持开放和好奇的心态,松散型无结构地汇集,正是这种连接的实现。这种合作,更好地包容了各种力量,为各种潜在可能提供了生长的空间。
“聚簇”(assemblage)是 Deleuze和 Guattari在同一本书中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哲学概念。和“rhizome”相同,它也是反对结构和反线性发展的。它是对社区等群体聚居状态进行固化边界理解的反叛。很多社会科学家将之称为聚集理论。它启发人类学家聚焦的问题不是简单地描述一个 “在一起”的状态,而是包括人在内的不同物种聚集后之间如何互相影响,相互生成。聚集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集居状态,提供了多样性生成的时空。它所代表的不是以往所理解的历史决定性,而是一种偶发的突变的非决定性,正像危机不是系统失调而是生存的条件一样。聚簇中充满了无意中的偶遇。这和网络不同,它强调的不是目的和理性。但它不仅排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且把这种批判带入到各种不同的物种中,产生于不同政治经济模式下的生物体在聚簇中相遇,对于人类学研究提出的问题在于,他们如何将简单的相遇转变为新的可能的发生?如果把rhizome作为一种知识的产出形式,笔者更愿意将assemblage理解为人类学对当下“emergency”成为常态的应对,是新型民族志田野分析和写作实践的一种试验。[9]它和拉图尔(Latour)的 ANT 理论相似,但是更加形象,更具有颠覆性。这也是很多从事科学技术批判研究、[10]全球市场研究的学者[11]对它青睐的原因。医学人类家劳伦斯·科恩(LawrenceCohen)和南希 ·谢柏-休斯(NancyScheper-Hughes),1999年开始了“器官守卫”的项目,在全球聚簇理论框架下,分析了包括器官捐献者、供给者、购买者、中间商、接受移植者等各个主体通过不同的政治经济技术规则联系的新的全球器官市场,他们的案例成为以往全球抽象/地方具体化两分法的替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各个具体因素的聚簇。
2009年,以美国加州大学SantaCruz分校人类学教授 AnnaTsing为首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两国6位人类学和地理学领域的学者在《美国民族学家》AmericanEthnologist杂志以松茸世界研究团队(MatsutakeWorldsResearchGroup)的名义发文,Anewformofcollaborationinculturalanthropology:MatsutakeWorlds,[12]为文化人类学家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合作试验,无论是其采用的搜集资料方法还是论文的写作方法,都让人耳目一新。文章是以研究团队为作者,包括五个独立部分,既有 TimothyChoy和ShihoSatsuka合作以 MoguMogu笔名出现的小章节,也有其他四位研究者(LiebaFaier,MichaelJ.Hathaway,MiyakoInoue和 AnnaTsing)以个人名字撰写的独立段落。让人欣喜的是这种类似rhizome的形式运用,和很多比较常见的合作形式不同,它既不是多篇单独作者独立文章整合在一起的杂志特刊,也不是一篇多名作者联合署名的学术论文。作为整体,如果隐去作者的名字,它完全满足 AmericanEthnologist对于研究型论文一致性和连接性的审稿要求,文章有导论,有方法,有数据,有讨论,有结语,篇幅也控制在25页左右。然而更为可贵的是,如果读者把每一个作者的独立署名的部分从整体中剥离出来,它也是一篇精致的自成体系的学术小品文,理论框架、研究对象与方法、数据分析、田野反思和讨论一应俱全,完全有独立成章的发展潜力。抛开方法论不谈,单就写作形式而言,就足以看出研究团队对rhizomes所反映的哲学理论思考,并将其付诸实践的匠心独具。合作民族志研究成果初具雏形。AnnaTsing将 MatsutakeWorldsResearchGroup的合作称为一直处于进行过程的合作和“强合作”,用以强调这种新型的文化人类学领域中合作的过程性以及在这种合作研究中对过程的关注。这种合作非常精妙地体现了 “块茎”所体现的生存形态:合作是辩证的而非综合的;对不同的声音不是消融,而是展现,多重声音又恰恰是这种合作有效性和高产性的表现;合作所描述的不同田野地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案例比较研究,而是商品流通所建立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也不是消融在所谓的世界体系之内,合作的知识生产方式应当与以往的概而化之、集而聚之的传统方式格格不入。时隔6年,AnnaTsing新的民族志专著TheMushroomattheEndoftheWorld:onthePossibilityofLifeinCapitalistRuins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精装出版。在前言中,作者明确指出,这本书是松茸世界研究迷你系列的开篇之作,“把它视为探险故事的序幕,它的剧情将随着相继的书一一展开,对松茸世界的好奇不可能被一本书一个声音所穷尽,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书分解”。[13](Pix)与此同时,AnnaTsing还指出对松茸世界的展现形式将会多种多样,不仅仅是学术专著和论文,还有影视和网络世界。
松茸世界团队的研究是全面的创新性“合作”试验,这不仅仅表现在其方法论的选择、具体搜集数据和写作技术的应用,同时也包括他们的研究对象———松茸世界本身。松茸作为一种新的跨国流通商品,其产业链连接着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松茸世界包括采摘者、科学家、交易者、森林管理者、市场销售者、消费者等多个行动主体。在这个网络中,合作不仅仅存在与人类学家之间、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学术界与非学术界之间,也存在与人与自然界之间,围绕松茸产生的生态世界中所有的行动者都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在这里经济、政治、生态融合一体,松茸是植物、食品、商品,也是环境政策的产物,松茸研究给我们展现的是在松茸场域中所反映出的各种力量和各个主体交会共生的一种物质、符号、社会权力关系的各种机缘巧合的“合作”。在 AnnTsing的作品中,松茸的世界是全球市场中的一种“聚簇”。美国-日本的松茸供给链中,尽管松茸的采集者所形成的“独立商业”模式,强调自己自由职业和对工业化劳动的抗拒,实践着非资本主义的社区生存,拒绝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超强的利用能力,他们采集的松茸蘑菇却经过购买者、批量收购者、出口商、进口商等多个环节,被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这就是所谓的残余积累。这里的运作方式明显区别于福特主义时代的流水线分工,而是更价趋向与以沃尔玛为代表的用信息技术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经济模式供应的物品迅速商品化。聚簇理论框架的使用在此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新兴的科技以及环境文化批判研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AnnaTsing的民族志不仅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极大的生存能力,也用诗一般的语言向我们解释了松茸蘑菇的文化世界———它是后危机时代的合作生存隐喻。松茸是无法人工培育的,是必须依靠自然界复杂生态环境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种真菌。“当1945年原子弹爆炸后,整个广岛成为一片废墟后,在这片荒瘠的土地上出现的第一个生命物就是松茸蘑菇。”[13](P3)它所激发的文化想象和生产的文化符号是“奇遇”“不同纬度的连接”“机缘”“变废为宝”、无法控制和预测的供给和危机中的重生。当全球频发的环境和经济危机剥夺了每一个人以往对于未来控制中的安全感之后,是松茸带给了自然界的礼物和生命的希望。松茸总是生长在被深层毁灭的树林中。松茸是后危机时代的隐喻。它体现的是对现代化分工控制承诺的希望的埋葬以及应对危机的合作生存模式的庆祝。合作是为了生存,但是此处的生存不是现代性所理解的个体对他者的竞争的胜利,而是对他者的生成。危机不是系统失灵的产物,而是生存的条件,危机让我们承认自己的脆弱和对他者的需求,它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所谓 “征服扩张”只不过是一种想象中的童话,历史更多的是一种被他者转变的生成。合作需要察觉和感知,而不是计算和推理,察觉和感知微不足道的连接,接触所生成的转变。就像松茸采摘者要有着灵敏的直觉去捕捉松茸的气息。
三、合作民族志试验中的困难与前景
合作研究试验在人类学界的发展无疑实现了很多理论创新,松茸研究团队尝到了学术共产的乐趣,对当下鼓励滋养个人寂寞的学术体制也起到了触动和批判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合作尚处于试验的阶段,它所面临的困难不容忽视。
第一,学术机构的相关制度限制,仍然以单独作者的论文和论著来评判衡量一个研究者的学术水平的高低,最终决定职称评定等晋级决定。这使得年轻学者的参与度降低。松茸研究团队中无一例外都是已有相当学术成就和影响的资深学者。与此相反,就笔者的观察和体验,在市场研究与咨询领域中,一些小的初创公司会更为看中集体的合作,但是随着其经济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专业化程度加强,标准的流水线作业增多,市场需求的焦虑和压力的增加,这种合作的精神和实践便日趋减弱,创新意识也随即逐渐消逝。
第二,学术界各个学科的“地域”意识仍然很强,其学术评价体系(如学术刊物、作者顺序、科研项目资助来源等等规定)经常有各自不同的具体的规定,无法真正达成共识。
第三,合作研究仍然会有权力关系的问题,尤其是合作者之间存在等级高低、资历深浅、经济资源多少等区别的时候。这种现实的权力关系是潜在合作的最大威胁。是否能够保持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使“债”的关系良性循环,让各个合作方感受到自己和集体创作的乐趣,是合作关系是否能长期维系的关键。当学术界和市场研究、咨询等部门合作的时候,因各自目的不同,对彼此的定位不同而缺乏共同的研究语言时,最终可能不欢而散。尽管这种合作形式有着多种资源优势,也为各方提供了资金、入场、关系、信息等多种便利,但这是一种权力关系不甚平等的合作,如果不能对合作各方的不平等关系进行公开讨论,对权力方进行制衡,这种合作有着潜在的深层危险性,处理不好可能最终导致学术界沦为政府和市场的共谋者,不仅无法产生有创造力的观点,而且也无法承担学者应当承担的呼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和义务,失去应有的批判立场。
笔者认为对于这种形式的合作,在中国现有学术生产体系内,应该慎重取舍。权力者对自己在合作中的权威地位如果不能够自省,学者如果不能做到真正有担当,那么这种将各方紧密联系的合作应该暂时搁置。
人类学界合作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开讨论的试验,不仅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经验。但可贵的是,当前很多知名人类学家仍然在坚持探索着,比如,GeorgeMarcus与艺术家的合作,PaulRabinow[14]与科学家的合作。前者因为合作而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成功地举办了体验艺术展览;而后者则基于自己失败的合作经验,详细论述了他理解的人类学家对生物科学技术研究的合作的贡献,即为科学家提供批判性的思考和思想工具。在中国,这样的试验也正在进行中。北京大学的赖立里等人类学家与来自7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医药相关人员通过一个关于少数民族医药的人类学研究项目,共同生产有关“民族医药”的知识,并将这一“合谋生产”的过程经由不同的研究者/研究对象共同记录在2014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当中。[15]这无疑是对多点民族志与合作研究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本土化实践。合作试验仍在继续,人类学家还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研究工具,经历着从孤独的独唱者的存在到集体的创造者的生成的转换。
[参 考 文 献]
[1]卢成仁.明星广告、“赫耳墨斯”与田野报告人:合作民族志的一种可能 [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3).
[2]ChaseR.TheRiseoftheColaborativeEconomy[N].JapanTimes,2010-10-4.
[3]RilesA.IsNewGovernancetheIdealArchitectureforGlobalFinancialRegulation?[A].DiscussionPa-perNo.2013-E-1[C].Tokyo:BankofJapan,InstituteforMonetaryandEconomicStudies,2013.
[4]RabinowP.AssemblingtheContemporary [M].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ChicagoandLon-
don,2011.
[5]MarcusG.Introduction:NotestowardanEthnographicMemoirofSupervisingGraduateResearchthroughAnthropology’sDecadesofTransformation[A].InFieldworkIsNotWhatItUsedtoBe:LearningAnthropology’sMethodinaTimeofTransition[C].JamesD.FaubionandGeorgeE.Mar-cus,eds.Ithaca:CornelUniversityPress,2009.
[6]StrathernM.TheRelation:IssuesinComplexityandScale[M].Cambridge:PricklyPear,1995.
[7]MarcusG.Ethnographyin/oftheWorldSystem:TheEmergenceofMulti-SitedEthnography [J].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1995,Volume24.
[8]DeleuzeG,GuattariF.AThousandPlatea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M].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7.
[9]MarcusG,SakaE.Assemblage[J].Theory,Culture&Society,2006,Volume23.
[10]RabinowP.AnthroposToday[M].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3.
[11]OngA,ColierSJ.GlobalAssemblages:Technology,Politics,andEthicsasAnthropologicalProb-lems[M].London:Blackwel,2004.
[12]MastsutakeWorldsResearchGroup.2009.Anewformofcolaborationinculturalanthropology:Mat-sutakeWorlds[J].AmericanEthnologist2009,Volume36.
[13]TsingA.TheMushroomattheEndoftheWorld:OnthePossibilityofLifeinCapitalistRuins[M].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rincetonandOxford,2015.
[14]RabinowP.AssemblingtheContemporary[M].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ChicagoandLon-don,2011.
[15]赖立里.多点、合作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医药调查的启示[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作者简介]
朱剑峰 (1976~ ),女,河南郑州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博士,主要从事医学人类学方向的研究。上海,邮编:200433。
董咚(1977~ ),女,上海人,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播学博士,主要从事媒体社会学与健康传播方面的研究。香港,邮编:999077。
编辑:张路尧
联系我们
复旦人类学之友读者邮箱
fudananthro@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