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ussig, Michael. “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atient.”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4B: 3-13, 1980.
摘要
作为现代性的某种体现,生物医学的功效被越来越多的现代人视作是灵丹妙药。在这种专业的霸权之下,医学、医生与患者陷入了某种技术至上的死循环:医疗从业者并不考虑疾病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而患者唯现代生物医学技术马首是瞻,放弃了应有的自主权。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与理想中的“人文关怀的医疗”渐行渐远。
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Michael Taussig(迈克尔·陶西格)因其在人类学领域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概念的运用而声名卓著,而他同样将这种颇为尖锐的见地融入了他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之中。在他1980年撰写的 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atient (物化与病人的意识)一文中,Taussig 就以此提出了不同于凯博文医学人文理论中“生物科技”与“人文关怀”分立的二重性的全新思路。

躺在吊床里的 Michael Taussig
Taussig 在开篇中直接引用了卢卡奇与马克思所提出的“物化”概念。物化(Reification)的本义,指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使得人自己被自己劳动所创造的物和制度所控制,人成了物的使役,人与人的关系也因此被掩盖。Taussig 认为,“起源于身体的社会语言被生物符号所掩盖和操纵”,符号、症状与治疗所体现的人类关系被神秘化,疾病获得了一种“虚幻的客观性”,而关系被伪装在“客观实在的科学”的意识形态之下。医患关系同样如此,作为一种社会层面的互动,其中隐含着无可避免的权力关系,甚至是一种赤裸裸的物化关系。
Taussig 同时关注了生物的身体与社会的身体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之下,他认为现代医学所关心的往往是如何(how)治愈疾病,而对病人所关切的为何(why)产生疾病的问题却视若无睹。他引述了普理查德的《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与魔法》,在阿赞德人的本土医疗实践中,这些问题往往是重叠的,而现代的医疗实践刻意地将问题分开,强化了对治愈方式的关注,忽视了疾病背后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使得医疗成了一种失却人性的冰冷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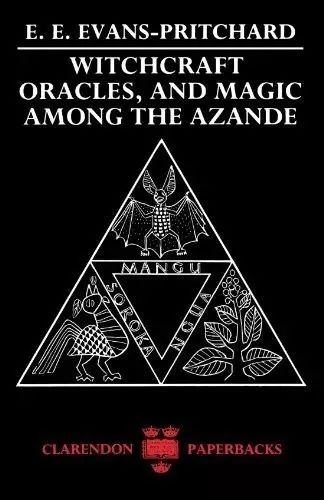
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名著《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与魔法》
随后,Taussig 以一位罹患多发性肌炎的病人的疾痛叙事为例,论述了医疗实践中的“物化”的可怖之处。在他看来,人所创造的医学知识与医疗体系,却使得病人受到医疗权威和专业主义的规训与管控,疾病成了一种脱离病人、脱离社会关系的客观事物。人不仅被疾病所折磨,还要被医疗体系与权威所驱使,使得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失去了自主权,病人的自我理解和自主能力被各种医疗分析手段(例如所谓的 S.O.A.P 方法)所异化(alienation)。在这种体系下,就连病人因为焦虑和不满而把杯子扔到地上的行为,都被护士的报告理解为“某种器官性脑部症状的证据”,结果这段记述在精神医师的诊断中竟然成了“精神疾患”的事实!在医学的笼罩下,疾病仿佛变成了独立化的、难以受控的客体。
即使医疗从业者认为 S.O.A.P 等方法是医疗实践中对人道的回归,然而 Taussig 认为,这种按部就班的操作步骤也是一种物化的形式──仿佛是商业生产的步骤。这种物化(医疗商品化)的倾向,在医疗实践中的合约(contracting)中最能得到彰显。在医疗服务中,医者和病人签订合约,看似明确了双方的界限并且增强了病人的自主权,但合约却让医疗的过程变成了福柯笔下的“规训”,病人的每一天似乎被合理分为治疗时间和病人自主的时间,背后却是无止境的条条框框和对病人的服从的高度要求。合约,这种本应见诸商业领域的事物,在医疗过程中成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恰恰反映医疗关系已然被当成一种物化的“商品”来处理。合约下的所谓病人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种遗患无穷的幻觉。
而在最后,Taussig 回顾了凯博文对“疾病”(disease)和“疾痛”(sickness)的二分,认为凯博文的论述提出的是一种“临床现实的文化建构”,强调的是将文化和社会的因素引入医疗实践来考察。然而在 Taussig 的眼中,“疾病”与“疾痛”的二分,以及医疗中引入文化因素的做法是无法治本的,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临床医疗对文化和社会产生的建构──文化的临床建构(Clinic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e),而这才是最应该受到关注的议题,或许也是解开现代医疗失却人文关怀困局的一种途径。
Taussig 的这篇论文距今已有三十余年,但其中呈现出的尖锐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在医疗技术与治愈手段不断发达的今天,生物医学已经日益成为了一种看似无法撼动的绝对权威。作为现代性的某种体现,生物医学的功效被越来越多的现代人视作是灵丹妙药。在这种专业的霸权之下,医学、医生与患者陷入了某种技术至上的死循环:医疗从业者并不考虑疾病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而患者唯现代生物医学技术马首是瞻,放弃了应有的自主权。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与理想中的“人文关怀的医疗”渐行渐远。
复旦人类学 石潘瑾欣 推荐
汪醒格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