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able monster and commodity cuteness: Pokemon as Japan’s new global power, Anne Allison.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6, No. 3,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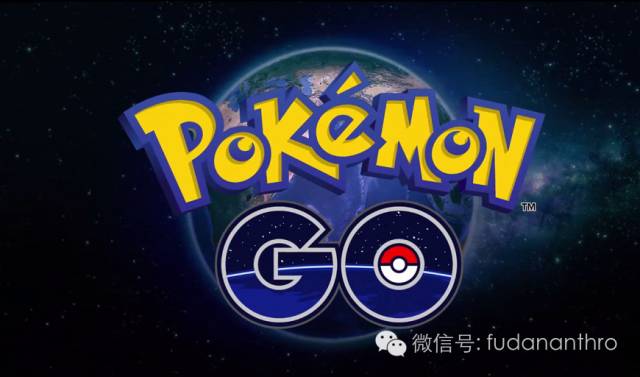
前些日子,日本著名游戏公司任天堂(Nintendo)与Niantic合作推出的手机AR游戏“Pokemon GO”一经上线便获得了全球追捧。彼时,从欧美到日本乃至港澳台,大街小巷一度都是拿着智能手机去捕捉小精灵的玩家,其盛况空前甚至引起了社会问题。看似简单的游戏,火爆的背后是宠物小精灵系列(Pokemon,中文官方译名为“精灵宝可梦”)20年来的长盛不衰。宠物小精灵的全球性成功,背后的秘密是什么,是科技?是营销策略?还是对玩乐、幻想和想象力的建构?而日本在儿童娱乐的领域,是怎样与美国的好莱坞和迪士尼分庭抗礼,最终获得一席之地并发挥全球性力量的?安·艾莉森(Anne Allison)的这篇文章,就是在尝试着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这篇文章从“小题大做”的意义上说,类似于艾莉森在1991年的《日本母亲和便当》一文:90年代的艾莉森从日本母亲的便当盒中瞥见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功能和意义,而在千禧年过后,她从Game Boy与宠物小精灵的世界里望见了“可爱”与情感、消费与商品以及媒体与技术这数者之间孕育出的全球性现象。艾莉森认为,诸如宠物小精灵这样的玩乐领域(playscape)经常被概括为一种具有“可爱特性”(cuteness/可愛さ)的事物,这种可爱的特性带来了受众对这些想象的创造物(比如小精灵们)的依恋,这种依恋与受众的童年和日本传统文化发生了共鸣,融入到受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可爱的特性又被包装在一个极为消费主义的、高科技而便携的形态(比如Game Boy这样的掌机)之中,伴随着这个形态和商品化的进程风靡全球。
主流的观点往往认为,宠物小精灵的成功源自于其跨媒体的展开、成功的营销以及其所具有的“玩乐”概念。艾莉森并不否认这点,不过她认为更重要的则是“可爱”这个特性。这种特性定义了宠物小精灵本身,引起玩家的关注,激发不同国家的人对日本的兴趣,给玩家们带来了一个与众不同、充满趣味和多样性并且舒心的幻想世界,最终成为了这个国家对外输出的文化资本。而且,宠物小精灵所植根的源头——掌机游戏是一个极具互动性的载体,它使得幻想的世界走进了玩家的日常生活,融入了孩子们的生活方式。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ANA)的“宠物小精灵”彩绘747客机
“可爱”本身在日本的兴起和认知也值得玩味。艾莉森考察了日本人认知中的“可爱”,以及可爱在产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发展的历史。在日本人眼中,“可爱”与“依赖”(dependence/甘え)和“温柔”(gentleness/優しい)紧密关联,而这种特性在日本人看来是可以购买、消费和培养的。可爱在日本的发展源自于战后日本经济的高度繁荣,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可爱产业”,从玩具开始,逐渐扩散到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可爱角色的品牌代言”成了一种时髦。可爱角色在日本被认为是适用于定义个人、群体、企业乃至国家身份的象征,因而我们在今天都能看到日本这个国家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象征着日本社会方方面面的可爱形象(熊本熊、哆啦A梦、凯蒂猫等等)。而真正定义了“可爱”的,是日本这个国家对可爱的高度迷恋。这也就是为什么宠物小精灵系列会选择皮卡丘,这样一个可爱、极具亲和力却又不失力量感的小精灵,作为这个系列自身的代表性角色。
GAME BOY COLOR游戏+“宠物小精灵 黄版”的机卡组合特别包
“可爱”不仅笼络了受众的心,定义了这个国度的某种特质,而且还关联起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与童年记忆。可爱这一概念本身与舒适、温暖相关联,带来的舒适感和慰藉,使得人们能够通过这些东西追溯自己的过往、怀想自己的童年。有学者认为,对可爱事物的消费与迷恋,源自于日本20世纪70-80年代的消费主义,而少女(shojo)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会为了自我的愉悦去购买可爱的东西。这种乐趣与日本社会(学校、职场与家庭)中对规训和表现得严苛要求是相对立的,在日本,规训的要求成为一种不分男女的社会压力,但是对于未经人事而暂时无须承担母亲角色的压力的少女而言,她们会较少受到社会期望的局限,因而有自己的空间去追求“可爱”的事物,以此消减压力、破除生活的条条框框。不过,这种起源于少女的兴趣,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扩散到整个日本社会,而不再局限于“少女”这个群体。
“可爱”关联着日常生活、童年记忆,减缓着个人生活中的压力,同时在儿童的成长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宠物小精灵的游戏设计者田尻智(Tajiri Satoshi)曾经坦言,他的目的在于创作一款同时具备挑战性和可玩性的游戏,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并且在后工业社会中给孩子们一个减缓成长压力的途径。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忙于工作的父母疏于陪伴,导致饱受孤立的孩子不得不在“影子家庭”——幻想中的角色、人工科技以及虚拟世界之中,寻找自己的亲密感与依附感。艾莉森认为,进入千禧年的日本面临着人性的丧失,而以宠物小精灵为代表的内容,是一种对未被工业资本主义所统治的往昔世界的怀旧,而事实上,田尻智创作宠物小精灵的灵感,正是来源于他童年在自然中捉虫玩耍的记忆。
可以通过联机通信进行互动的GAME BOY游戏机
宠物小精灵为孩子们提供了虚拟的、却又充满真情实感自我空间,不仅成为了孩子们面对学校和家庭压力的缓冲带,帮助他们度过成长过程中的艰辛时光,而且还通过每一代游戏所具有的通信技术,鼓励孩子们通过高互动性的便携媒介与其他孩子交流(收集与交换小精灵)。对于孕育出无数“家里蹲”的内向性的日本社会来说,这种鼓励玩家“走出去”交流的游戏方式,确实是独树一帜。便携的媒介,创造出了便携的陪伴,而孩子们与小精灵的羁绊,则孕育了一种“口袋里的亲密”。
当然,艾莉森不曾忽视宠物小精灵背后的资本主义本质。虽然宠物小精灵等等的内容排除了人们的孤独和压力,“治愈”(healing)着后工业时代日本社会的人性缺失,但它的本质仍然是商品。这些商品在发挥着孩子们想象力的同时,仍然充斥着对获利的追求。当治愈与可爱的玩乐伙伴无处不在、遍布日常的时候,商人们也就能最大限度地获利。对艾莉森而言,这个时代的商业领域遍布着如同传染病毒般的欲望和商品(commodity),而我们的一切都受到这个商业领域的形塑,宠物小精灵也不能免俗。宠物小精灵的主题曲中有一句歌词:“我要把它们都抓住”(Gotta catch'em all),而在之后的艾莉森看来,这恰恰反映了一种贪婪,一种“无处不在的迫使人前进的驱动力”,使人追求一个无休止向外延伸的边界,延伸到更多的消费之中(Allison,2006:278-279)。对艾莉森来说,宠物小精灵既是便携的幻想伙伴,也是新世纪的资本主义流动的形态。
在最后,艾莉森仍然注视着宠物小精灵的价值。她说,正因为有了宠物小精灵这样的产品,日本的文化产业才能在网络科技与后工业的社会化时代中,碰触到新世纪的儿童的脉动。他们把灵活性与幻想融入到极为便携的科技手段、亲密而可爱的虚拟物以及繁多复杂的商品形式之中。同时,从全球视角来看,在宠物小精灵融入全球儿童娱乐的商业领域的同时,日本也将自己置入了全球文化的图景里。世界的文化产业因此从传统的欧美主导,逐步呈现出去中心化的态势。
艾莉森的视角和思路在十余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麻省理工学院的文化人类学者伊安·康德瑞(Ian Condry)认为,艾莉森的日本玩具研究对“构建文化世界”的议题提供了独到的视角,启发了他对于日本动画产业“创造力协作”的探索。而在我们看来,艾莉森笔下的宠物小精灵,兼具可爱的特质、商品的流动性和资本主义的逐利性,在影响着全球受众的同时,不断地闪现出新的思想火花。
复旦人类学石潘瑾欣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