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wis,Oscar.1966.The Culture of Poverty. ScientificAmerican, 215:1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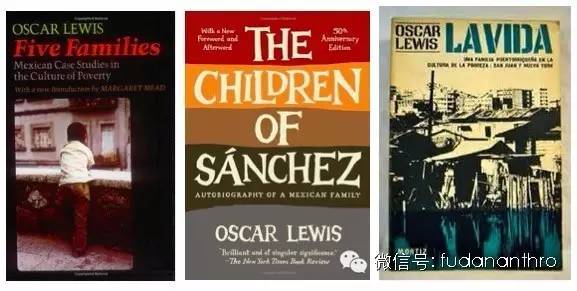
在20世纪美国人类学界,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可能是除了米德和本尼迪克特之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公共政策制定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唯一一位人类学者。从1959年到1966年,刘易斯出版了以墨西哥和波多黎各移民的“贫困亚文化”(后简称为“贫困文化”)为主要研究议题的三部在学界内引起反响的民族志。在刘易斯看来,贫困并非只是物质资源的匮乏,而是由此导致的阻碍穷人改变自身境遇的文化价值观。此后,他把针对特定族裔人群“贫困文化”的研究发现加以总结,写成高度概念化和公式化的《贫困文化》一文发表在1966年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之后,“贫困文化”一词顿时成了指代所有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特殊人群的标签,不胫而走,最终对以弱势族群为援助对象的美国社会福利政策修订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或者说是“恶果)。
如果仅从财政层面考虑,在西方社会消灭绝对贫困现象,并非难事。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脱贫费用与当时全国烟民一年的买烟花销总和大致相当。事实上,如把这笔脱贫费直接交到穷人手里,那么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将超出贫困线。那么为什么这一在常人看来用财力即可解决的问题,反而成了困扰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一大顽症呢?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决策者在解释贫困现象采用的两种思路:一种是将贫困归咎于个人;另一种则是从社会结构中存在的个人所无法抗拒的力量中找原因(即适当地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多数情况下制定具体政策时占上风的是第一种思路。认为穷人应为自己的悲惨境遇负责的看法,在西方社会由来已久。诸如19世纪济贫院之类解决贫困问题的机制,是建立在一种认为贫困是缺乏个人努力或由于病态所致的想法之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们通常会对穷人有这样先入为主的假设:缺乏技术知识和向上的动力,学习和工作能力均低于常人,而且道德涣散、体质匮弱,故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支撑这种假设的常识是:人的社会地位是其才能和努力程度的必然反映,即:能者成功而无能者失败。这种常识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的英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精英的共识。当然,这些精英从未领过分毫福利补助,对穷人缺少必要的了解,自然对贫困现实一无所知。在当时执政者开始实行“劫贫济富”的大环境下,许多学界内外人士开始从穷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他们对生活的期望,而不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本身来探讨贫困的原因。为这种偏见提供部分理论支持的,正是来自人类学家刘易斯的“贫困文化”概念。
在特定的田野语境里,刘易斯力图解析“穷人之所以受穷”以及贫穷如何塑造穷人人格的问题。他将贫困和与贫困相关的一系列特征统统视作一种自成一体的亚文化,一种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尽管他对造成“贫困文化”的政治背景(如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有所揭露,其主要的研究目的则在于通过建构和运用“贫困文化”概念,来阐释穷人的人格行为以及持续性贫困的原因。他将穷人,尤其是在居住在北美的墨西哥拉丁族裔移民,刻画成挥霍无度、缺少时间观念和行事规划以及充满旺盛性欲的“特殊人群。”正是由于穷人的这种特殊心理行为特征,使之陷入穷困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而今,绝大多数在墨西哥或者拉丁族裔社区做过田野研究的人,都会毫不犹豫指出:刘易斯用于阐发“贫困文化”概念的理论框架实在过于简单,难免会犯认识论方面的低级错误。城市人类学家布古瓦(Bourgois)根据自己在纽约东哈莱姆波多黎各移民居住区历时三年的实地调查经验,对刘易斯的“贫困文化”学说,有如下中肯的评价:“刘易斯的方法植根于弗洛伊德式的文化以及在50年代主宰人类学的人格范式。他没能注意到个体的生活是如何受制于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结构。30年之后,我们以一种后见之明,不难对他的这一过于简单划一的理论框架进行批评。在刘易斯对一贫如洗的波多黎各移民所作的简约归纳式的心理描述中,看不见有关阶级剥削、种族歧视,当然还有,性别压迫,以及特定语境中文化意义的微妙之处”(Bourgois 1996:16)。
社会学家莫雷(Murray)通过阐发刘易斯的观点,形成了他的“依存文化”理论:在福利社会,老弱病残孤寡者属于一个特定范畴,以政府救助而不是进 入劳动力市场,自谋出路为生存手段 (Murray 1984) 。这一不断成长的“依存”亚文化起到了削弱个人奋斗的意志和自我救助的能力。也就是说长期享受福利救助的人已经过惯了饭来开口的日子,缺乏自谋出路和自食其力的动力和斗志。一些通过问卷访问得到的数据,似乎为“依存文化”的说法提供了有力住脚。在美国前总统里根执政期间相当得势的保守势力也不断通过传媒,企图向纳税人传达这样的信息:接受福利救助者由于缺乏自身努力,理该受穷。
总之,刘易斯的观点难以摆脱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特有语境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现代化理论追捧者的说法。在自由市场条件下,所谓成功人士的多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冲劲,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资源以及将工作效益最大化的价值观。与此相左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通常被看作是穷人特有的消极特征以及穷困之源。虽然,刘易斯本人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一度向往社会主义(曾接受卡斯特罗邀请前往古巴居住生活),他在研究穷人的生活方式时中却很少强调社会结构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刘易斯成书的20世纪60年代适值美国政府调整制订一系列“向贫困宣战”的福利政策。而旨在消除贫困的任何来自决策层面的动议,都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么是以经济制度这一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源头为目标加以攻克;要么是以改变穷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为目的。最后多数反贫困的福利改革都是以改变穷人的“落后”价值观和“不良”行为扶贫的最终目的。由此可见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说”这一原本为人类学家错用文化概念的“无心之过”, 对福利政策的制订和修改,的确产生了不利于维护穷人福祉的副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在扶贫研究过程中,也不由自主地将刘易斯的“贫困文化”作为立论依据,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概念产生的政治背景及其被用于政府决策后产生的不良后果。对于当今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来说,刘易斯“贫困文化”研究留下的最大教训是:用民族志来讲穷人的故事,必须格外慎重小心,必须看到比“文化”更强大的结构性力量,必须让自己的人类学想象力屈从于“社会学的想象力”。
参考文献
Bourgois,Philippe. 1996. In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lls, C. Wright.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见中译本:《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
Murrary, Charles A. 1984. Losing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复旦人类学 潘天舒 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