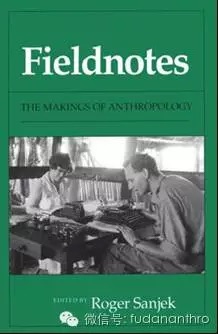
Sanjek,Roger. 1990.
Fieldnotes: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标签:田野工作
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言中说:“想象你自己独自一人,突然到了一片热带沙滩上……想象你自己第一次进入了村庄……”也许,就是一片茫然。田野工作对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更是充满神秘性。原本这么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知道怎么进入田野,知道要观察什么,记录什么,然后从田野中退回来思考,获得一些新的洞见,这自然是最美妙的。殊不知,这背后有多么不确定,一份经典的人类学作品,或许真的可遇不可求?
最典型的人类学家做田野工作的形象是,在“那里”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参与观察,并写日记做记录,然后回到“这里”写文章。具体整个过程却不为我所知,想要还原一次田野工作经历,人类学家的随笔似乎是不够的,可最原始的田野笔记又难见庐山真面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想要弄清楚一次田野研究中,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关系网络,终究不能获得圆满。
著名城市人类学者桑杰克(Roger Sanjek)编纂的这本题为《田野笔记:人类学是这么玩的》(本人意译)的文集中论述了关于田野笔记的很多吸引人的话题。全书由五个被分散拆开的章节组成。
一、与田野笔记一起生活 (Living with Fieldnotes)
第一部分中,Jean E. Jackson在她所写的“我就是田野笔记:专业认同符号的田野笔记”一文中,就访谈法的运用对一个考古学家、一个心理学家、两个社会学家、两个政治学家和一个语言学家进行了访谈。主要议题涉及田野笔记的定义、导师和训练、分享田野笔记、保密性、死亡、有关田野笔记的感觉、田野笔记作为一种人类学家创造的独特文档。
在这一章中,原来很多被访者说他们也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做田野笔记的指导,即使得到过田野工作训练的人也认为众口难调,很难用一门课程去应对不同风格、不同研究兴趣和不同环境的田野工作。他们的训练也恰恰反映了田野工作和田野笔记的神秘性,就是说,学习的唯一的方法是通过“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即sink-or-swim)的方法,你依恋、你灌注心力、你真正被激发起来,也只有这样,每个研究的地点不同,研究计划不同,人类学家也不同,人类学也不是一个你能知道最好方法的舞台,而且由于理论和方法的新旧之争,田野笔记训练的传统也不可能出现。①Jean E.Jackson在结论中还说,研究生训练中,那种“故意不知道任何事的精神”的暗示也恰恰是促使学生成为人类学技艺的积极的创造者或者再创造者这一隐藏课程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子,那么反倒可以说,即使不太知道田野工作的具体技术,也没有关系,只要去做就好了。
桑杰克在这一部分中的文章是“天灾人祸和魔法师的徒弟”,主要讲了田野笔记的物理遗失和精神分离。田野笔记凝聚了田野工作者的很多努力和精力,它满载着人类学家的情感,也能够揭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唤起他的职业感、个人胜任感和责任感,它的物理遗失便是一个人类学家最糟糕的事儿了。事物总有两面性,有时候“写出一篇引人注目的民族志最好的方法就是丢失了田野笔记”,此时能自由地代表事实来说话。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利用、回忆和增补田野笔记的努力。田野笔记是珍贵的,短期看是人类学家自己的面包黄油,但是长期来看它就像是一个孩子,不会是其作者的私人物品,正如最后的那首诗写到“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他们通过你来却不是从你那儿来,尽管他们跟你在一起却不属于你,你能给他们身体的住所却不能给他们灵魂的居处,因为他们的灵魂居所是你不能访问甚至都不能梦到的明天……”用孩子之于父母来比喻田野笔记之于其作者真是妙绝了。
二、打开田野笔记 (Unpacking “Fieldnotes”)
第一篇文章是James Clifford的Notes on Fieldnotes.他分了写的三种类型,Inscription,Transcription和Description。这是三种相互联系的写的形式。相对而言,Inscription程度最浅,就是快速记录下一个观察或者某人刚说的话,这个过程最能体现田野工作的混乱和不可避免的灵活性以及记录数据的挣扎努力。民族志是一个完美田野笔记中的纯粹的Inscription成,这样子的观念却因为Inscription是在记录者的选择和控制影响下而受到冲击。实际上有关事实的Pre-figuration和Pre-encoding的理论也使得Inscription的原始性受到质疑,因为观察者不会单单收集和记录信息的。Transcription就是转述已经形成的和固定的论述或者知识。Description就是或多或少更对观察到的文化事实的更加一致连贯的描述,这产生了格尔兹所说的“浓描”,Description更加注重反思、分析和阐释。在这里,三种写的场景是在一系列偶遇、感知和阐释中混合或者快速转变就是田野工作。
第二篇文章是Rena Lederman的Pretexts for Ethnography: On Reading Fieldnotes。田野笔记是一种很奇怪的文体,既是田野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民族志的一部分,也为这两方面所形塑。同时,它是针对自己的,绝大部分人类学家在拥有自己的田野笔记之前是没有读过其他人的,也没有现成的好的模式可以参照着做。读自己的田野笔记如果说感觉到不舒服,除了因为它涉及到了个人的焦虑和不足,或者模棱两可,还因为它很危险,原本是记录下观察来辅助记忆的,实际上它却挑战记忆,使人回到了不确定性之中去,田野笔记可以反对民族志撰写中所鼓励运用的单一的人类学的声音。说到有方向感或者迷惑的时候,Rena Lederman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讨论了个人日志、每日笔记和整理打印的文档,每一种记录田野数据的形式对读者来说都有明确方向感和迷惑的感觉。比如说个人日志,对特定问题有着详细和综合的描述,是自己对事情如何契合在一起的感觉的记录,显然有着比较明确的导向。在另一方面,对整体的感觉却很难连贯一致,因为这种对田野整体的这种感觉一直在变化而且来源很多,熟悉的“这里”将另外一个世界纳入关系之中,不熟悉的“那里”通过大量写作。
那么怎么利用这些田野笔记呢?Rena Lederman说首先用来自我澄清,试着去捋顺自己的知识的时候,往往能够发现不协调的或者遗漏的东西。对踏着田野工作日常节奏的田野笔记的分类也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沉淀。另外一个利用田野笔记方法有关于它的自我维持,这是为了作报告和确认不同于形塑田野日记的情境。田野笔记通过描述事件并探寻事件之间的联系来定向确认,也就是说基于事件来记录,因为事件有着明显的完整性,助于感知到当地的逻辑和兴趣,而且再次阅读事件导向的笔记增大了发现笔记之间新的关联的可能性。田野笔记的最后一个作用就是整合到民族志的撰写之中去,使之有一种相对的不单一的声音。也许通常的民族志写作引导着读者以小说方式看世界,然而用一种没有导向的写法反倒可能激发读者去再思考新的分类和视角的再定位,也是很有意义的。
这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是Roger Sanjek的“有关田野笔记的词汇表”。主要介绍了田野笔记的相关词汇,比如Headnotes、Fieldnotes、Scratch-Notes、Fieldnotes Proper和Fieldnotes Records。Headnotes很巧妙地形容对田野的感觉,这种感觉显然是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础之上的,Fieldnotes写下来在之后是不会改变的,而Headnotes却是可以变化的。Fieldnotes在田野里产生,那么Field在哪里?田野不一定非得要跟旅行联系在一起,有时候田野就单单与注意力和惯常社会联系的转换相关,田野笔记是关于田野的,而不是在田野里的。Scratch-Notes的生产就是之前所说的Inscription,把Scratch-notes转换成Fieldnotes这个过程还是一个Description的过程,Fieldnotes Proper就是一般说的“Journal”“Notebooks”“Daily logs”。Fieldnotes Records又可以称作数据,是独立于连续的田野笔记的信息。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在每个研究计划中独一无二的问题。分支学科和方法的要求促使人类学家直接去收集Records,相应的Fieldnotes Proper就减少了。如果说要真实地去描述个人行为和思想的话,没有Fieldnotes的Records可以说是危险的。为了平衡这两者,the Johnsons提出了一个文化情境清单,作为将整体性关怀重新引入田野工作的中介。Texts就是由transcription产生的文本。Journals和Diaries服务于分类梳理的目的,长期建构的Journals是田野笔记和记录中的信息的关键,而Diaries则记录了民族志学者个人反应、挫折以及田野中生活和工作的评估。Letters、reports和papers,书信往往是田野工作者写给导师同学朋友亲人的,记录自己的心理状态,并且是一种不正式形式的描述和综合,在这里,这是将Headnotes转化成paper的第一步。最后一种田野笔记形式是录音文字还原稿。
三、田野笔记实践 (Fieldnote Practice)
第一篇文章是Simon Ottenberg的Thirty Years of Fieldnotes:Changing Relationships to the Text.作者将田野工作与童年进行了类比,一方面,在田野中作者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者,能够自己做决定,这种兴奋感却被抑制了,因为需要不断的报告导师,他总是在那儿,这就像是一个发展一个自我的同时却丢失了自我。另一方面,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要学习语言和规则,要学习怎么生存,以前的经验没有用,或者根本起相反作用,在田野中依赖于翻译、田野向导、一起住的人以及朋友,学文化的时候就像是个孩子,当得到了一些知识和经历的时候,就有了一种成长的、青年的、成熟的感觉。田野笔记恰好就反应了这个“文化童年”。同样作者还提到在他内心的个人不朽和个人成功的欲望。
在这里Ottenberg 阐述了Headnotes,就是脑海中的田野工作的记忆印象,写下来的笔记其实压制了很多鲜活的记忆,虽然Headnotes也会被曲解、遗忘、精心设计或者屈从于作者自己的田野的刻板印象。虽然写下来的笔记还是那样,但是作者在交流、教学、写作等活动以及自己学术的越加成熟之中,headnotes改变了,对写下的笔记的解读也转变了。Headnotes和Written notes其实就是这样子在不断的对话之中。Ottenberg还觉得在田野中写作是一件困难的事儿,因为在田野中有着自己的个人关系,写作会带来时间和精力与田野工作的紧张冲突,而且在田野中爆炸性数量的数据也很难使人能看到秩序。田野笔记就是代表着无序和不规律,这是相比较出版的作品和Headnotes而言的。如果说Fieldnotes是一个童年成长的物质象征,那么Headnotes就是一个人类学家不断成熟和独立的成人自我,它们之间有着持续的对话。那么,远离田野的写作就包含着Headnotes更多曲解的可能性,尽管这也提供了一种重新整理数据的机会。在这里,Ottenberg承认自己毫无疑问地陷入了殖民网中,但是他并不后悔或者感到羞耻,因为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批判当时殖民意识的学者也就是没有意识到当下的政治氛围,在现在的框架中过去显得很同意理解,但是又该怎么应付对现在这个世界的误解以及对研究的影响呢?人类学理论在不断变化,文化中心主义、整体性取向、实证主义等等的被新的理论所取代,Ottenberg发现自己的笔记代表的正是那已经死去的传统,尽管如此,他把自己的田野笔记看作是自己作为人类学家的童年和生命,早期的田野笔记也是自我服务的,但较之自我理解,更侧重于个人的提升和成功。事实是文化相对主义被文本相对主义所取代,所研究的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观念应该转变成为阐释和阐释者的,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阐释,文化是一种被阐释的文本,田野笔记也是一种文本,生活在一个解释学的,象征符号的和隐喻分析的世界之中,人类学有一种很强烈的审视自我的转向。而所有的这些却使得Ottenberg能够继续用他的殖民笔记来写作,只要把这些田野笔记看做是文本就好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具有讽刺性的意想不到的扭转。同时,作者发现,在他在其他理论指导之下得来的数据,也能够用当今的理论和术语来重新解释,即使这些不是新鲜的数据。如果说写的东西并不是客观的,而是阐释性的,这样子的理解,反过来,却也作用于田野工作,使得能够得到更丰富的洞见。Ottenberg还觉得人类学转向了自我、自己的人类学过程、反思和文本,部分的就是对一些不幸的话题的回避、一种对研究过的人的现状的失望的抵抗机制。自我的取向,不应该仅仅是对自己,还应该是对所研究的人们的自我的研究。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保罗·拉比诺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提到的,对他的助手马里克的变化的认识,在马里克的图式中,不是用社会经济阶层来理解村庄的,而在拉比诺的催促下,他才尝试将每个人纳入特定的阶层,这个时候马里克新的自我意识和原来的自我形象截然不同。当所研究的人们为了人类学家把自己的世界对象化而自我反省的时候,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过程。
第二篇文章是the Johnsons的Quality into Quantity。人类学跨坐在科学和人文的边界上,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每一步走向科学的信度不可避免的就与人文的亲密关系远了一步,许多层次的人文主义的阐释的成就也是以科学的准确性作为代价的。站在科学研究的角度,首先,人类学笔记常常是记录观察和印象,试图描述多种多样的事件、感觉和想法的散文性文本,即使在作者头脑中有图式来指导,但是田野笔记却没有显然的编码图式,以至于不能够马上定量化,甚至不能简单归类成分析性分类。其次,大多数质性研究设计的松散性导致了极度费力的像真空吸尘器般的综合收集。最后,这个在小社会中的参与观察,反复记录的还是那些人,这就损害了合理抽样程序中的“观察的独立性”标准。但是,如果把田野笔记限定在基于合理抽样和测量的数据,那么问题又来了,首先行为主义科学家从来不会知道他们的研究主题,研究对象要是不信任研究者就很有可能保留或者歪曲信息,不能保证效度。这第二个批判就是严密的推导性的研究设计常常就是简化主义的,用几个变量来解释一个现象。人类学中的科学和人文貌似很难调和,极端的定性定量二分法也是不可取的,在不损害科学和人文的整合性的情况下定性的资料也可以转换成定量的数据。问题是需要确定一个笔记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文化事件的样本?如果按照以下三个程序做的话,这也是可以解决的。首先,如果没有偏见地出现在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的面前那样子的话,就这笔记会是事件发生的代表性样本,其次,如果倾向于没有偏见地记录被访者的所有生活方面的话,这笔记也会是一个代表性样本,最后的话,就是说如果在理论性的合适的方法上来对事件进行分类的话,那么也会产生有意义的事件的计数。前面两点是抽样问题,最后一点是测量问题。越发地去遵从前两点的话,就越接近整体论观点。人类学整体论的核心意义就是文化是一个整合起来的整体,个人只能在整体的上下文情境中才能被理解。整体论对人类学家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想法一种技术,还是最基本的一个责任,科学和人文的人类学的最基本的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世纪后半期,人类学却从整体论中游离开去,这也许就是人类学科学方法论渐强的结果。从科学主义角度来看,人类学整体论是一个模糊的混乱的想法,聚焦的研究计划一开始就拒绝了整体论,而且作为专家有责任少关注研究计划之外的东西。其实人类学家有责任来提供一个围绕着特定研究焦点上的情境资料,这样子,其他研究者就能有机会用整体的数据来批判和扩展分析。
整体性田野方法存在描述的地点偏差和内容的偏差。任何影响人类学家何时何地进行观察的偏差性就会在田野笔记中反应出来,而减少这种偏差的方法就是运用时间分配的方法进行随机性的观察。聚焦于某个问题的研究设计总会或多或少将研究限制在特定方面而没法把握全局,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是时候去重新思考缺少推断性理论的旧式样的整体主义和缺少综合性的现代特殊主义。研究者最好在进入田野的时候有一个聚焦的特殊问题,同时有一张整体主义的清单来提醒他们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东西。总结起来看的话,案例计数确实提高了田野笔记的精度和完整度,其可能性也由于处理文本的电脑软件而大大提高,虽然人类学田野工作不可避免是存在偏见的,但是通过随机化方法和整体性清单,仍然有可能使田野笔记足够能代表一个共同体的整个社会和文化生活。
这一部分最后一篇文章还是Roger Sanjek的The Secret Life of Fieldnotes.这篇文章主要是讲了田野笔记的历史,对此的叙述,散落在个人田野工作记录、论文记录的报告性辑录,民族志的前言附录、旨在方法论的论文,对人类学的历史性研究中,以及Cushing、Boas、Malinowski和Mead等人类学家的日记和信件中。在下面的文章中,主要介绍了Frank Hamilton Cushing、Franz Boas、W.H.R.Rivers、Bronislaw Malinowaski和Margaret Mead这五位基于田野工作的人类学的奠基人的田野经历和贡献。Malinowaski提出的Speech in action就是指除了询问资讯人 ,人类学家还要在日常生活的自然背景中倾听当地人的交谈,如此记录下来的数据对Malinowaski努力达到的抓住当地人的观点、他们与生命的联系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这也恰好是参与观察的核心。
1920s到1960s是古典时期,人类学从文化主义-功能主义-整体主义转到了对互动、个人行为和复杂性的不断增长的兴趣之。美国的人类学家带着一个特定的问题开始田野工作然后从那儿扩展开来,从Transcription转向了 inscription 和description,从文本转向了Fieldnote和Records,而英国的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缩小他们的研究,让问题在田野中出现,整体主义的田野笔记也试图覆盖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
从1960s到1980s这段时期总体说来结构主义和象征人类学不需要广泛的田野笔记,文化生态学也不需要。认知人类学也是需要正式的记录。结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在象征人类学中,田野笔记更加重要,它集中于实践、行动、互动、活动、经历和表演,集中于行为者、能动者、人、自我、个人和被访对象,还集中在交换、投射、生涯、发展周期等等。
接着Roger Sanjek论述了Speech-in-action和访谈的田野笔记。凡是谈话事件在资讯人的领地上的就是Speech-in-action,在民族志学者自己这边的就是访谈。根据谁控制着谈话这一标准Speech-in-action和访谈还能各自分为三种情况,资讯人控制说什么,民族学家试图控制谈话以及协调的共享谈话权力。这样子的分类有助于民族志学者对症下药。
四、流通中的田野笔记 (Fieldnotes in Circulation)
第一篇文章是George C.Bond的Fieldnotes:Research in Past Occurrences.什么是田野笔记?George C.Bond在这里说到它至少包含着两种系列的品质,写下的文本和话语。话语是有意义的行为的瞬即的谈话,包含四种品质,它是在临时和现在中实现的,它是自我指涉的,总是有东西要表达,也是交换所有信息的中介。文本是一种更加去情景化的话语,把特定的说话者和地点移开,在实践之外的语言和社会系统中重构它,文本是固定的、自动的、重要的和开放的。
田野笔记既不同于文本,也不同于话语。文本把写作和阅读分开来了,读和写之间没有直接的交流,而田野笔记是由读者写的,每次阅读都是一次对话,一次他们跟现实和田野数据中记得的经历的关系的追问。田野笔记建立了与过去的时间的对话,它也只是一部分固化的话语。田野笔记是复杂社会历史结构的部分构建,是协调了的和破碎的现实过程的一部分,在当地的向导、资讯人、我们的观察和理论的相互作用之中建构起来的。它是多声道的产物,是实验、转述和阐释的角斗场。它也是收集、协调建构点滴现实的行为结果,所以它能暴露出参与观察的弱点和强势之处。
最后一篇文章是Roger Sanjek的Fieldnotes and others,田野笔记的最开始的关系就是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而这篇文章则讲到了田野笔记跟其他人的关系,比如资讯人、其他学者和学生、工作组以及田野笔记传承之人的问题。在做田野工作的时候,在资讯人面前做笔记或者根据记忆来写笔记,在一些特殊的仪式庆典时当地人十分希望人类学家当场做笔记,有时候,人类学家把写作、整理笔记、分类法、地图和机械帮助等直接展示给资讯人以获得支持。 像Mead和Ottenberg等人把他们的田野笔记给他们的学生看,这不是一种对如何做田野笔记的说教,而是田野笔记的分享,这种分享仍然是比较少的,而且集中在比较亲密的关系之中。越来越多的田野工作不是像马玲诺夫斯基那样单枪匹马,而是组织化的团队研究,在这样子的团队努力中,田野笔记的角色和流通形式各异。比如调查员做快速记录,此时还有一个平行进行的拍照或摄影观察者,这样子的结果就是非传统的以照片为基础的行为分析。如果说草稿没有及时誊出来的话,就会影响内部交流,没有人会读过所有的田野笔记,这对团队的整合来说不是好事,设计者如果每隔一段时间跟其他田野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报告、讨论、记录田野笔记然后根据主题做检索和分类,这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过程。关于田野笔记的传承问题,当Headnotes随着人类学家的死亡而不复存在的时候,只剩下了写下来的Fieldnotes,但存留自己的田野笔记对人类学家来说也是一个按不确定性,矛盾和预设的。
五、从田野笔记到民族志 (From Fieldnotes to Ethnography)
最后一部分内容是很精彩的从田野笔记到民族志。决定性战斗不是在田野中的战斗而是之后的工作。David W. Plath写了Fieldnotes,Filed Notes and the Conferring of Note。对田野工作来说,能够计数起来笔记的页数,录音的时间,胶卷的长度,就是衡量工作量的标志。对文件工作来说,从短期来看,特别是在形成专论或者可视化文件的时候,你最好的活动指标不是产出,而是扔掉。从如此多的资料中筛选可以是一个令人却步的工作。不容易解释的是很多人类学家公开讨论其职业活动时候的甚至都羞于提到文件工作。在这个论题上的唯一的评论是米尔斯的“On Intellectual Craftsmanship”(心智的手艺活)。 米尔斯描述了他自己的文件,如何用在智力生产中?他的答案是这种文件的保持就是智力生产,他的文件是一个不断增长的事实和想法的仓库,从最模糊的到最精巧的。
此外,文件工作中可能确实有一大翻恭维的话,伪造数据和捏造事实。但是作者嗅出来的最浓烈的味道不是这种腐败,而是这种努力持续承受的泪水和汗水。
不论是在田野还是在文件中,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理解工具持续的是人类的搜寻“是什么”内在的敏感性。人类学通过宣布一种最适应生存的现象来引导我们的这种搜寻。但是在做田野笔记和组织记录文件的时候,不仅仅是抓住和传递信息,更卷入了社会行动,这些社会行动带来特定人们和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公共媒体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一个社区或者一个个人或者一个事件的时候,他们就将一些社会意义注入其中,还有潜在的力量。对这个过程很敏感的人就能够期望将这种敏感性转移到更新的境地中去,特别是到人类学的田野中去,看看当地人关注什么,搜寻“是什么”。
Roger Sanjek最后给我们奉献上的是一顿关于民族志学的效度论题的大餐。到底是怎么“写起来”?拥有资料只是一件事儿,用资料是另外一件事儿。写作最开始需要一个结构化大纲形式,这就是索引。做索引的过程就告诉我们民族志是怎样构建起来的。怀特是以他研究的群体作为基础来分类索引,随着资料的增多,记忆可能都不容易定位了,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初步的索引系统,分三栏的页面,分别写上访谈观察的报告、日期和研究对象,以及简单的总结,这样子需要3到8页,需要回顾这些笔记的时候,只要读索引就能回忆起笔记完整的画面。Wolff发展处一个主题分类,产生了66个标题,分为了7大类,包括背景材料、文化变迁、社会关系、社会设置、评估或解读、模式的线索、理论和方法。而这样子的检索也会随着田野工作的进行而变化。
写作有时候是一个社会过程,马林诺夫斯基在做出详细的大纲之后,就会与他人讨论交流,更典型的是,很多民族志写作是在田野工作之后,利用Headnotes和Fieldnotes独自写出来的。写作,把民族志学者从发现的情境逮到了报告展示的情境,马林诺夫斯基对田野笔记的持续分析,他的田野工作的方法,第一层是孤立事实的观察,具体活动、仪式或者行为准则的记录,第二层是把这些机制联系起来,第三层是各个方面的综合,这样子就很容易转入展示报告的情境中。而怀特很清楚简洁的说明了写作方法,他说,在写作报告的时候,可以直接把索引做成论文的大纲,几分钟的对索引的再读就能得到一个系统想法。然后根据每个话题,就能把访谈数和相关材料的页码写到大纲上去。精读索引能够更新对访谈的记忆,回忆起是不是重复了一些东西。人类学研究讲究的是效度而不是信度,人类学是在效度语言上来表达的,比如机制、模式、结构、大纲、网络、组织、关系、地图、网格等等这些都是在讲是不是说了自己声称的内容,这就是效度问题。人类学效度衡量是根据三个准则的,理论的坦白、人类学家的足迹和田野笔记证据。人类学田野研究有很多选择,对于选择的理论性原因的解释是必须要讲清楚的,重要的理论决定了带入田野的地点、问题和记录目标,这水平的理论把田野工作联系到更大的社会、政治、符号和经济问题中去。此外,田野工作者还发展起来了重要的关于人、时间和地方的地域性特殊理论。很坦白的对什么时候为什么在当地发展出重要理论的表露也是提高人类学效度的方法。作者同时问了不少关于理论的问题,哪里的理论?在田野中或者在田野之外。什么时候的理论?计划田野工作的时候或者形塑研究指导方向的时候。为什么要理论?给人类学意义和目的,避免所有事物的乐观研究。哪个理论?必须要诉诸于政治和批判价值。搞明白这些问题,在理论的坦白这方面,效度就大大提高了。
人类学家的足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则,观点很简单,就是说任何有效的人类学家都发展了田野工作过程中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网络既是研究事业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其结果,所以如果把这个网络更详尽地分类,而不是单单的以日期分类的话,就能得到一个珍贵的额外的视角。重要的资讯人不仅提供了大量信息,而且将人类学家介绍给其他的资讯人。从田野笔记中,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公开重构资讯人联系的图。
第三个标准是田野笔记证据。Headnotes的证据会在民族志中得到证明,但是,田野笔记就很少得到公开的检查,对田野笔记和民族志的关系的一个解释也是衡量效度的很重要一个标准。一种是围绕着巨多田野笔记材料组织起来的民族志。一种是利用情景分析或者说扩展案例方法来组织的民族志,原则在一个一个案例中和相关参照中重复出现。还有的常常利用缩进的从生活史访谈材料中来的小点来显示这民族志文本的效度。大多数民族志中田野笔记和资讯人的声音常常被有规律地筛掉,就显得是远距离的人类学家在讲述。叙述和修辞决定主导了“写”,田野笔记的出现不是为了效度而是为了这修辞或叙述的手法,这就不得不面对这难以理解的包袱了。田野笔记的多声道模式就寻求与资讯人分享民族志权威,就像交响乐一样,Clifford就真心提倡将资讯人也作为作者列上去,资讯人的文章也要与民族志学者一起发表。所以说,仍然需要去思考不能用自我和他者这两分法来预测的人类学。
最后Roger Sanjek引用了爵士发明者Miles Davis的话,“你需要知道号角,知道和弦,知道所有的调子。然后你忘记所有的东西,只是演奏。”知道人类学的传统,知道田野工作的方法,知道什么组成了民族志效度是需要的,但是这并不能产生民族志。就像爵士,人类学需要即兴演奏的人,不仅知道这么做,而且就在做的人。
复旦社会学 王淑茜 推介
参考文献:
[1]RogerSanjek.Fieldnotes: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2][英]奈吉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
[3]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4][美]威廉·怀特,街角社会[M].商务印书馆.1994
[5]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6][澳大利亚]林恩·休谟.人类学家在田野[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