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ground Introduction
本文作者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是墨西哥裔美国人,美国纽约大学人类学系荣休教授,亦是人类学后现代思潮中的一位代表性学者。其最著名的田野工作是对于菲律宾吕宋岛上伊隆戈人(Ilongot)猎头(head-hunting)传统的考察。其第一任妻子,人类学家米歇尔(Michelle Rosaldo)于1981年在回访伊隆戈部落时的意外身故不仅展现了田野考察的危险性,也是罗萨尔多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此之后他写作了《文化与真相:重塑社会分析》(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等著名作品。

本文是其于1992年发表的题目为“文化研究与学科:边界还存在吗?”的演讲底稿。在本文中,罗萨尔多就“文化研究”为人类学家和族群研究者带来的焦虑和可能性展开思考,并指出人类学和族群研究在以文学学者主导的文化研究领域中能够带来何种机遇。
原文系:Rosaldo, Renato. 1994. “Whose Cultural Stud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6(3): 524-529.
罗萨尔多首先指出了文化研究在当时美国学术界的一片热潮中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尽管文化研究成功关注到了过去默默无闻、或是对学科建树隐约具有威胁性的主题,甚至在某些领域内承诺它能够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但文化研究的学者在同行评价和资金支持等方面却始终受到学科划分的桎梏。而与此同时,文化研究却又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学术霸权”,不断侵蚀着既有学科的研究领域。罗萨尔多认为,这种矛盾所反映出的正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多分支知识运动”(multistranded intellectual movement)的独特困境:文化研究的多分支性意味着其难以在传统的学科划分体系中找到合适的定位,而这却是“学科化”学术体系的背景下中不得不做的。这导致的结果则是,文化研究学者不得满足两种体系——自身的跨学科构架和传统的学科划分构架——所提出的要求。此外,与其它跨领域研究(例如国别研究)相比,文化研究本身亦缺乏一种朝着学科化方向发展的动力。
接下来,罗萨尔多将目光转向文化研究的系谱学,梳理了其两大历史源流。他首先提及的一个源头是被他称之为“无形大学”(the invisible university)的读书小组(reading group)。结合他自身的经历,罗萨尔多认为读书小组往往涉猎广泛,开启了不同学科背景学者间的跨学科对话,将学术讨论从限定的学科框架中解放了来,并成为一种对文化精英主义和学科框架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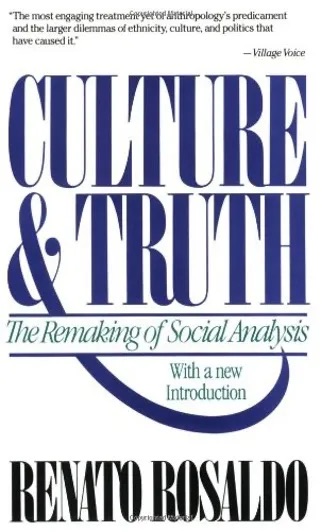
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缘起是以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E.P. 汤普森(E.P. Thompson)和葛兰西等学者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这部分学者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于人类解放的关怀之外,同样关注到了文化、意识形态和人类能动性等议题。罗萨尔多还指出,文化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文化和权力的交织互塑与另一股重要的学术力量结合在了一起:这股力量源自于女权主义等社会运动(包含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等),旨在将性别等从前被视作既定(taken-for-granted)且铁板一块(monolithic)的概念问题化,并对这些概念作出重新定义,同时指出这些概念的建构性和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罗萨尔多认为,这两股力量不仅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动因,对其他学科也同样有所裨益。由此,罗萨尔多在接下来的部分以“人类学家”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类学家(Chicano anthropologist)”两种身份,就文化研究与其他学科(主要是人类学和族群研究)互惠的可能性进行阐述。
他首先以人类学家的身份指出,人类学家对文化研究的回应往往是一种“受排斥的悲痛”(lament about exclusion):他们因没有收到文化研究的“邀请”而感到沮丧。在这种图景中,从事文化研究的文学学者往往以一种掌握权势的、霸权主义的、排斥异己的反派形象出现,而这些人类学家的回应则是,尽管文化研究不断强调其跨学科的性质,但他们始终认为它只是改头换面的文学研究,或是声称“文化研究从事的无不是人类学早已做过的”。在罗萨尔多看来。这种看法确有合理之处(例如文化研究从人类学那里借鉴的E.B. 泰勒式的文化定义,即文化无处不在、与日常生活所有方面紧密交织),但他也强调,人类学维度的文化意涵本身也同样在发生转变,其对象范围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扩散,也不再是一个封闭自洽的意义体系。与此同时,人类学也失去了对于文化概念的垄断,因为这一概念已经广泛为其它领域所采用,并被不断重新阐释。这种文化意涵的变化要求人类学家从研究实体(object)转向研究意义组织的过程(process),从研究单一文化转向研究跨文化交流,从研究异域文化转向研究自身。罗萨尔多认为,人类学内部的这一转向受到了文化研究的推动,它固然会导致某些人类学家感到失落,却是一种实质上的进步。也即是说,人类学亦从文化研究中有所获益。
但从一个墨西哥裔美国人类学家的角度来看,罗萨尔多认为文化研究带来的更多是焦虑。在族群研究领域的学者看来,文化研究不过是复辟白人男性权威的一种尝试。罗萨尔多认为,文化研究的问题并不在于将白人男性学者纳入其中,而是在纳入这些学者的同时却忽视了其它学者的声音,并把前者视作“the great white hope” [1]的归来。这导致了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与族群因素密切相关的诸议题却由一个只有白人参与的会议来主导讨论。尽管如此,罗萨尔多仍然抱有希望:族群研究是一支具有反抗性的学术传统,这种特征在主流学科中已经难以觅得,而文化研究则恰能够为族群研究提供一条进入主流视野的路径,但前提是对白人权威的复归保持警惕。换言之,他认为文化研究需要将其视野部分地转向本土语言、本土历史,与本土学者展开对话,尽管这将会、也应当导致全球化和本土体系的碰撞;同时,文化研究也应囊括不同学科的见解,尽管这会制造误解和冲突。从根本上来说,只有学术标准的根本改变才能够使文化研究获得更强的包容性和更高的学术质量,而在这些方面,罗萨尔多认为文化研究无疑能够从族群研究领域借鉴大量的变革资源。
最后,罗萨尔多从学术实践的角度为美国学界的文化研究提出一些发展的可能性。例如,回溯文化研究的源头“读书小组”,在制度性的学术体系之外开辟一个更具包容性、更少边界感的新领域,并向一个更加公共化的学术领域迈进。我想,这不仅仅是文化研究的一个目标:对于美国人类学而言,在本尼迪克特和米德引领的人类学黄金时代过去之后,应该朝着何种道路发展,而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人类学而言,该如何解决自身独有的学科问题(无论是学科划界,学科融合,还是学科互鉴)、又该进行怎样的自我定位,这些议题无疑都值得进一步的思索。
注:[1] 这一短语的本意是“被给予厚望的人”,但在这里,罗萨尔多借用“white”的双关含义,暗指文化研究领域中白人学者被视作解决一切问题的“救世主”,而其他少数族裔学者的声音却被忽视的现象。
复旦社会学 王若旸 推介
潇月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