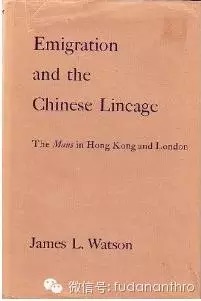
本周推荐:
《移民与中国宗族:文氏族人在香港和伦敦》
James L. Watson. 1975. 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 The Mansin Hong Kong and London.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全球化、跨国移民、认同、多元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些年来成为社会科学界的关键词。学者们仿佛找到了一片新大陆,旧的理论图式和方法论似乎就此被推翻或者至少被重新定位。然而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种种新知,最健康的学术态度应该是“温故知新”。阅读人类学家屈顺天(James L. Watson)1975年出版的关于新界移民村(侨乡)的民族志不仅丰富我们关于移民、社会组织这些经验问题的知识,同时有益于重思人类学知识本身。
1969年,屈顺天和太太华若璧(Rubie Watson)前往香港新界研究农村。如果严格遵循当时汉学人类学界的学术传统,他大概只会再写一部“传统”中国村庄的民族志。当屈顺天抵达新界新乡时,他发现当地的文族的壮年人都在忙着去英国打工;但与此同时宗族的种种公共活动依然盛行。在一个社会科学界“现代化理论”流行的年代,(现代的)流动性强的移民和(传统的)稳定的宗族组织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这个出乎意料的社会事实却成为人类学家屈顺天全书关注的主题。一方面,他关注宗族组织在组织移民过程中扮演的作用;另一方面,作者考察了移民对侨乡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屈顺天在田野实践中勇于摆脱当时风靡一时的认知人类学范式的束缚,从而使其研究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植根性和前瞻性。
作者首先追溯了这些新田文族人决定移民的社会情境。在上世纪中叶,大量来广东的的移民在新界开始种植蔬菜,并且获得不菲的利润,传统以种植水稻为生的文族人对这些勤奋的大陆移民和他们从事的蔬菜种植业不屑一顾。但随着蔬菜经济的发展,当地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与此同时来自东南亚其他各国的大米开始进入香港,卷入市场经济的文族人在种植水稻上很难有利可图。从1960年代始,大部分文族人就开始放弃种植水稻,却在当时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职业。文族人从心底上瞧不上那些没有土地,在集镇上工作的劳工,觉得他们像水牛一般地工作;与此同时,由于教育程度的限制,他们又不能做技术工人的活。在1957到1962年之间,一些文族人在周边的集镇当商人和小生产者。“这些从前的农民没有什么商业知识。他们并没有去慢慢学习怎么做生意,而是直接去投资如纺织厂,零售店,西药房这样的竞争性企业。对于他们来说,成功失败与运气息息相关。就如他们种田时依赖于运气。”只有少数从前有一些商业经验和广泛人脉关系的文族人在集镇做生意取得成功。总之,周边城市为他们提供了很少的机会。与此同时文族人并不只是偏居一隅的村民,他们的生活早就与更广阔的世界发生着联系。1950年代之前(最早的船员起始于1885),新田就有一些人定居在欧洲。他们有些是从前的海员,有些是在二战中跳船的“非法移民”,这些船员大都来自贫穷家庭。屈顺天在田野中遇到了一些退休的船员(其中一个退休船员就出生在牙买加),他们大都回到村里依靠自己的亲戚安度晚年。
伴随着英国50、60年代的餐厅热所带来的劳工需求,骄傲的文族人开始远渡重洋企图改变自己的处境。一批在当地通过土地中介、赌博操作和边界走私生意积累起资本的文族人开始去英国开餐厅,另一些文族人随着在这些中餐厅工作。在学术界开始大量关注移民和全球化进程之前,这些被认为是“落后”的文族人就开始过上了全球生活。
而屈顺天也早在大家还在关注封闭的农村社区,移民研究未流行之前,问了一个移民研究最为重要的问题:移民是如何组织的。他细致地记录了文族人是如何筹旅费(有些富裕的族房有一些公共基金,但大多数人通过在村外自筹或者是工资相抵的方式),如何跟移民局处理官僚手续(村委会起着重要作用),宗族联系如何在找工作和筹集旅费扮演中介作用。
而早在“多点民族志”被提出之前,屈顺天就开始在跨国语境中关注文氏族人在新田和移民英国之后的生活。文族人在海外并没有形成什么组织,大多数餐厅工作人员疲于应付日常生活,英语水平有限,没有太多时间投入社区活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觉得将来会回乡,他们最为重要的参考群体还是新田文族。他们跟家乡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寄钱回来,装修房子,给宗族捐献,办酒席。这些活动一方面为了名声,另一方面也是为未来退休考虑。屈顺天也同时观察到移民对农村社区所发生的变化。随着移民,新乡从一个生产场所变成了一个消费场所。土地不再被视为重要的财富来源,文族人把大量的钱投向私人房产。随着大量的移民外出,留守的老一代男性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无聊感,于是花很多时间玩麻将。而随着新的工作机会,年轻人获得了更多的婚姻选择权。虽然移民后大家收入多有差距,但相对于从前依赖于土地的数量和宗族地位的地位获得模式,屈顺天认为移民具有平等化效应。令人遗憾的是,屈顺天在这里将收入的差异归功于个人原因,没有细致地思考社区内的不平等(华如璧的理论取向与他在这一点上有较大的区别)。
这是一部朴实无华却令人回味无穷的民族志。为什么?读完这本书,我发现这些陌生的文族人如我的近邻。我对他们的处境充满同情心和理解——为了骄傲的活下去远渡重洋;但偶尔也对他们暗暗不爽——自己在外是移民却照样在家里歧视从大陆来的新移民。好的民族志在于呈现人类状况的复杂性(现在的种种理论还没有真正开始考察普通人动机的复杂性!),而不在于简单粗暴地揭露制度的罪恶。其次,在方法论上,屈顺天在人类学家开始讨论单一村庄研究的缺陷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广泛参照引用前辈和同行的研究(如陈达1938年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在当今充满竞争和火药味的学术界,这部民族志的模范作用超越了文字本身。
好的民族志总是历久弥新。在当今中国与世界相遇中,过于执迷于“新”有时只会让我们愈加焦虑不堪。如新乡这样的农民(或者是欧洲今日的温州移民)或许让喋喋不休谈论“世界”的精英们所不齿,但我们不得不正视他们开启了一个草根全球化的进程,这对我们与世界相遇和理解世界有着重要意义。
在这项研究之后,屈顺天继续了很多研究, 其中包括著名的麦当劳研究。但他说自己研究的灵感总是来自他在新界认识的这些村民和朋友,他只是一个记录者。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大陆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开放,香港在人类学地图上变得没有从前那么重要,对中国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开始行走于广袤的大陆地区,捕捉迅速变化的社会图景(如所谓的从社会主义向后社会主义转型),尝试各种新鲜的理论范式(试图突显中国研究对整个人类学的贡献)。然而我们是否因此更加了解中国和世界吗?
推介人何潇为复旦人类学2008级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