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因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引发了各界对中医药的新一轮热烈关注和讨论。其实人类学家对中医的研究热情由来已久,本周推荐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詹梅教授于2009年出版的关于中医全球化的民族志作品,以跨地方知识生产的视角来审视全球中医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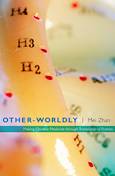
《想象世界:跨国视角内的中医实践》
Zhan, Mei. 2009. Other-Worldly: Making Chinese Medicine through Transnational Fram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这是一本以跨地方知识生产视角考察中医全球化的当代民族志。从理论和方法论脉络来看,作者詹梅从女权主义人类学(Feminist Anthropology)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Technology Studies)汲取养分,反思现代性对秩序、纯净的追求,强调知识生产过程的复杂性、片段性、变化性,借用海德格尔的worlding取代被普遍滥用、过于简单化、完美化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说法。
阅读这本书时,读者不必试图寻找作者对中医全球化宏大图景的描绘,她想要展现的本就是许多激发我们想象的、破碎而又充满联系的故事。1960年代,中医针灸被赞誉为服务于第三世界国家农村穷人的预防医学,象征着中非友谊和种族化的无产阶级世界,而1980年代以后,“与世界接轨”的中医传播转向东亚、欧洲和北美,针灸被重塑为一种关注全面健康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更加有趣的是,上海的中医很快融入这股新潮流,创造出“亚健康”这一被普遍误以为来自西方的概念,并为新兴中产阶级勾勒出一幅值得追求的美国式中产阶级生活景象。“仁心仁术”是传统中医实践的核心价值,商品化、市场化以及与西医的交锋对整体观的、人性化的传统中医实践提出了挑战。面对西医主导的边缘化处境,传统中医经常通过“医学奇迹”即强调中医在西医无力之处的效用来展现自身的合法性。在与国际学生的教学互动中,翻译并非中立的跨文化媒介,而是建构着跨地方的知识和身份认同。三位女性选择进入或离开中医的生命史帮助我们审视亲属关系和性别因素所扮演的角色。跨地方的碰撞并没有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形成统一的中医群体,尽管“美国”在中国对世界的想象中占据着亲密位置,“中国”对于许多非华裔的中医行医者来说在时间和距离上依然遥远。
作者认为,所谓“传统中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是产生于中西医相互碰撞纠缠的动态形式,相伴而生的是我们关于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所处位置的无定型的想象、理解和实践。作者并非意在提供一部传统中医的社会史,因为“社会”史的概念已经假设存在一个相对稳定、持久的知识核心的边界。她关注的是“行动中的”中医,中医的日常世界不仅仅局限于诊所和课本上的教条,还包括知识、身份认同、社群如何被建构的竞争性过程。
采用多点民族志的田野方法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作者最初只是计划在加州湾区做单点的田野,但她逐渐发现不能把研究对象从社会网络中强行摘出来,于是自然地被迫转向多点民族志。在这里,多点不仅仅是指加州湾区和上海两个地方,还涵括了中西医诊所、院校、病人、NGO等各种有助于理解“传统中医”从何而来的网络。
本书最值得人类学专业学生细细揣摩的亮点在于故事与分析的紧密联系。这体现了一种人类学家的气质:强烈的兴趣驱动、对冲突的敏锐捕捉、活跃的思维、丰富的想象……正如詹梅老师与我们分享的经验:人类学的精华不在于大的理论,而在于始终贴近人的方法,每一次田野都是全新的设计。田野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你已经知道的东西,而是打破常识。捕捉意外惊喜之处,在看似没有关联的现象之间构建贴切的分析,而非宏大的理论。
复旦人类学 沈悦菲 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