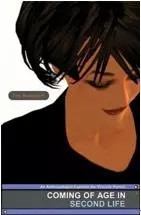
《第二人生的成年》
Boellstorff, Tom. 2008. Coming of Age in Second Life:An Anthropologist Explore the Virtually Huma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作者,是就职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人类学家汤姆·博勒斯托夫(Tom Boellstorff),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性别、全球化、虚拟世界、东南亚研究、艾滋病以及语言的人类学研究。
博勒斯托夫认为人类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她选择研究对象的弹性:就以他个人的田野研究为例,从印度尼西亚地区的同志文化研究到虚拟世界的赛博文化(Boellstorff 2008:xi)。
经典人类学著作,如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所讲述的是“真实的经验,真实的信仰与真实的生活”(Boellstorff 2008:4),而博勒斯托夫将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与理论,仅透过电脑显示器来研究虚拟的游戏世界。
他选取了第二人生游戏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该游戏是由林顿实验室(Linden Lab)开发的3D模拟现实的PC端网路游戏,玩家在里面可以进行空间开发、建立亲密关系,进行金融交易等活动。
为了探索人类学应该如何致力于理解虚拟世界的文化,博勒斯托夫“潜伏”于第二人生游戏中,他所使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参与观察和访谈,他的研究对象从物理空间意义上来说,散布于世界各处,但是线上活动都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但由于虚拟世界的研究实在是太新了,不管是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博勒斯托夫都有很多问题需要交代和澄清。人类学家能否纯粹在虚拟世界进行研究显然是存在争议的,因为线上用户仍然需要在物理空间中消磨他们的大量时光。
但是博勒斯托夫认为从“玩家的视角”来研究虚拟世界对于发展与反思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对于技术变迁对人类生活已产生巨大影响这一不可回避的事实而言是非常关键的。大部分的虚拟空间都拥有成千上万的用户,甚至更多。
如此一来,虚拟世界中不断发生地新的社会互动与意义制造的形式,人类学家需要不探索新的方法和理论来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
为了进一步丰富与明确作者的意图,博勒斯托夫用两条路径解释了该书副标题中所出现的“虚拟地人类”(virtually human)一词:
首先,虽然一些极具洞见的研究已经宣称线上文化(online culture)的兴起标志着“后人类”(posthuman)的到来,但是博勒斯托夫认为第二人生的文化在本质上还是“人类”(human)的。
不仅是是因为在第二人生这个虚拟世界中借鉴了太多真实生活的情境;虚拟世界也显示我们的存在其实一直依赖于“虚拟地”,这本身就已是我们成其为人类的根本特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虚拟世界与物理空间就完全无异了。
所以,博勒斯托夫对“虚拟人类”的第二条解释路径认为虚拟世界的活动对现实生活会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在虚拟世界我们又不完全是“人类”——人性受到空间制造、主体性以及社区转型的各种可能性的影响,它的平衡被打破,得以创新和重新第一。
基于这两条分析路径,博勒斯托夫写下了这本民族志。
联系到博勒斯托夫早期研究对印度尼西亚地区同志文化的关注,看上去似乎与第二人生的研究毫无关联。
但其实不然,博勒斯托夫在他的两项研究中都重点关注了自我(selfhood)与社会的问题,还有就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正如博勒斯托夫有意将书名取为《第二人生的成年》,他希望借此让人回忆起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那本名声大噪的《萨摩亚人的成年》(Mead 1928)一书,伴随20年后弗里德曼重返萨摩亚,关于此书的争论将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推向了风口浪尖。
虚拟世界的研究正是要挑战原来人类学家认为理所当然的田野边界与解释范式,认为这向来都是人类学家的一厢情愿(Gupta and Ferguson 1997),他们愈来愈意识到民族志研究不应该将其自身限制在一个单一的田野点,博勒斯托夫认为第二人生的研究就可以被视作是一个多点研究的项目(Boellstorff 2008:6)。
但自始至终,博勒斯托夫都认为对于虚拟世界的研究与传统的人类学并非人们想象的那般相异,他们都是期望以整体的视角理解当地人的文化。
最后他再一次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一句话,来表明自己对于人类学与民族志研究的看法:“民族志最终的目的永远都不能够丧失洞察力。简而言之,就是要抓住当地人的视角,他与生活的关系,走进他者的意义世界之中”(Boellstorff 2008:249)。
雷 婷 推 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