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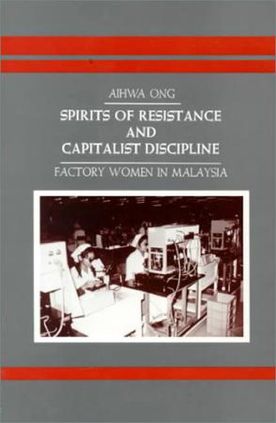
“为什么马来女工在现代化工厂的车间会发生阶段性的魂灵附体?”(1987:xiii)本书开篇的这一简单问句,开启了对于资本主义工作规训与年轻妇女雇工性别构建之间关联性的人类学探究。作者王爱华(Aihwa Ong)在1979到1980年间在马来西亚雪兰莪(Selangor)瓜拉冷岳沿海自贸区进行了为期14个月的实地研究,获得了来自档案、入户访谈、个案史和现场观察等不同来源的田野数据。从福柯到布迪厄、格尔兹、伍尔夫、陶西格(Taussig)和霍尔斯鲍姆(Hobsbawm)等大家得到的灵感和启示,为作者的故事讲述提供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本书聚焦马来西亚乡村在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不同阶段的文化抗争,透过来自农村的工厂女工的视角,展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训和渗透下这一新生女性群体与家庭、男性、村庄、劳动过程和整个转型社会的互动、调试与抗争。作者引入斯科特和福柯的观点试图向我们说明,20世纪末期的人类学不应该再简单地将权力关系理解为施加方与承受方,而应在强势权力与弱势群体的碰撞中看到她们怎样技巧性地向权力借力,根据不同势力在不同阶段的规训,在不同的生产生活领域,时而抵制,时而反击,时而协商,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构建并重构自身的身份认同。
作者首先借助历史资料向读者交代了马来西亚的被殖民背景。英国殖民统治不仅将新的生产和交换关系带给了马来西亚,同时也改变了马拉西亚农民与农业、土地和更广阔的社会的关系,乡村的马来人成为世界市场大量需求的橡胶和椰子的生产者。这些商品作物的种植除了使少数公务员变得富裕外,并未对马来的村民带来任何益处,相反,单一作物的种植使他们极度依赖世界市场,同时他们凭借热带雨林和海洋而自给自足的部落生计模式被打破,不得不开始购买工业产品,这种情况使得马拉西亚在独立之际,乡村地区开始出现贫富分化:少数得利的公务员统治阶层与种植商品作物的农民阶层。
独立后的马来西亚从国家发展计划、学校项目、福利设施、党派活动到宗教实践等各方面配合宣传执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发展”的名义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被鼓动从事工资雇佣劳动(wage labor),除了种植商品作物,政府设立了自由贸易区,凭借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引进大型跨国工厂。当不久前还处在部落社会的当地人的生活开始被学校的铃声和工厂的钟声的规律性管理时,人们对家中少男少女的期许也发生了变化:十几岁的少女被迫辍学去附近自由贸易区里的跨国工厂做工,赚工资来补贴家用,青少年男孩则被鼓励求学以便将来可以从事白领类的职业。在作者田野中的三家日本的电子企业负责人都表示,他们工厂车间里女性工人占比80%-85%左右,之所以如此倾向于选择女工,是因为这些公司大多秉持资本主义所奉行的脑力劳动优于体力劳动的观念,流水线的车间工人需要的技能低,在跨国公司整个架构中处于链条的最底端,这些辍学的少女们被认为是手指灵巧,智力迟缓(nimble fingers, slow wit),最能胜任这项工作。工厂仅用支付极少的工资,且不怕人员流失,因为每年还有源源不断的辍学少女涌入,可以保证车间的人力资源充足。女工们在工厂需要接受严格的管控,从穿工作服到工作时间再到车间经理和领班不断要求提高的生产效率,“效率、清洁、忠诚”这些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和价值观就这样从日本吹入了马来半岛的伊斯兰文化。公司倡导大家庭理念,希望员工不停歇地提升自己的技能,同时要对公司绝对忠诚,它们邀请女工的家属们参观工厂,并诚恳地希望其家人可以将公司的理念延续到家庭里,帮忙监督女性员工,提高她们的工作热情,并承诺会代家属们监管好外地的女工,不让她们接触工厂以外的人,以免因其性别的特殊性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然而,工厂的女工们还是成为了村庄里对传统道德的威胁。这首先体现在她们开始与家庭协商自己的婚姻。在有了经济收入后,女工们不但开始自己挑选未来丈夫,也决定婚礼的形式和婚后的居所。同时,经济上的独立使她们在休息时间可以穿上时尚的衣服去逛街、看电影,女工们的择偶范围也逐渐扩大,并推迟结婚年龄,还产生了一个新的交友类型——男朋友和一种新的交友方式——约会。这种现象受到了严厉的道德苛责,父母们认为女儿的行为给家庭蒙羞,舆论不断指责女工们的不道德行为,认为她们丢弃了传统的穆斯林少女(maiden)的价值观。话语即权力,言语是对现实经验的反映,工厂女工们在建构自身主体性时无法逃脱既有的社会观念,与男人一起外出,尤其是与非穆斯林的男人外出约会的现象同样遭到了很多工厂女工的批评。作者认为,虽说工厂女工们在受到工作的束缚之余获得了可观的社会解放,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阶级意识”,她们虽然不断追求自身经济条件的改善,却依然捍卫既有的社会观念,从来没有叩问整个男权主导的体制。
就田野语境而言,本书标题中的spirits一词至少有“魂灵”(鬼魂)和“精神”两层意思。也是就是说,附身于女工的“魂灵,”在实践中有“抗争精神”的功能。在作者看来,“抵抗的魂灵”是马来西亚工厂女工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最具技巧性的制衡,她们借用当地的世界观对资本主义市场关系非人化的面貌进行了道德上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传统马来社会对其性别控制的控诉,是马来西亚从道德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中女性在接纳自己新的主体性和新的认同的过程中的一种情感宣泄。女工们认为她们在工厂经常受到不公正待遇,工厂的工作强度非常大,精疲力竭的女工有时生病或者睡眠不足,但是领班们仍然不断要求她们提高生产效率,跟不上工作节奏的女工会找各种借口去祷告室或称女性问题去厕所,而在这两个地方她们经常被“鬼魂”抓住。同时,女工们的外乡男友,通常是工厂车间的领班,经常会在夜间被本地人袭击痛打或被当地青年警告不准与kampung地区的年轻女性约会,这种仇视外地男性的行为通常被当地的长者默许。马来西亚乡村地区的人们相信宇宙中住着各式各样的鬼魂,它们可以轻易地游走于人于非人之间,缺少对鬼魂警惕的女性会被愤怒的鬼魂附体。在自由贸易区的跨国工厂里,有时会爆发大规模的鬼魂附体,1975年一家美国电子工厂中有40名马来女工被鬼魂附体,工厂被迫停工三天,并请了一位灵疗师在车间里杀了一头公羊驱魂,美方主管不知道该怎么向总部汇报“8000个生产小时因为有人看到了鬼魂而丢失”。之后这样的事件频频发生,1978年一家生产显微镜的工厂中有120多名女工被鬼魂集体附体,同年又有15名女工被鬼魂附体,有部门负责人描述当时“有些女工开始啜泣,进而竭斯底里地尖叫,这尖叫声像会传染一样,整条生产线的女工都开始啜泣叫喊。”工厂又被迫停工三天开始驱魂。对于“被鬼魂附体”,女工们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因为身体太虚弱,有时认为是工厂太脏招致了邪恶的鬼魂,还有的认为是自卑情结让灵魂生了病。
通过作者翔实的田野资料与分析我们看到,在马来西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全球资本的生产方式、政府推行的政策与乡村的传统对kampung地区的女工在不同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控制,有时这些力量互通互融,彼此协作,有时这些力量所产生的后果彼此制约,在其中生活的女工们虽然没有强烈的阶级意识,也不曾与这些势力正面交锋,却技巧性地用自己的方式在不断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塑造并重塑自身的主体性。作者在最后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新的主导形式不断出现,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知识权力和生产体系越来越具身到社会关系中控制我们的生活,作者希望人类学家可以多倾听非西方世界的声音,观察那里的人们挑战主导势力所采取的多样性实践从而揭示现代性的多个面向。(其实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监控与规训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调适生活,这也许是你给某个给分总是很低的老师取的某个绰号,也许是你上班路上未按城市本来的规划抄的一条近道,也许是你趁海关不注意多带了几条烟,如此种种不正是构成我们生活乐趣不可或缺的部分吗?)
本书作者王爱华为加州大学伯克利(UC-Berkeley)人类学系资深教授。近年来她先后提出“文化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弹性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 和分级主权(graduated sovereignty)”等在社会科学领域全球化研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概念。作为成名作,这部《抵抗的魂灵与资本主义规训:马来西亚的工厂女工》在田野研究和理论探讨的深度方面,取得了足以与斯科特《弱者武器》(1985)媲美的成就。
长期以来东南亚一直是人类学家钟爱的田野乐园。解释人类学代表人物格尔兹曾在印尼的爪哇、巴厘岛进行深入的田野研究,援引马克思•韦伯“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之说,提出了文化作为“意义之网”的解释,从而使人类学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格尔兹被后人最为诟病的恐怕是女性视角的缺失和对文化中权力关系的忽视。王爱华的这部《抵抗的魂灵与资本主义规训:马来西亚的工厂女工》可以说非常恰当地展现了这两个主题,较好地弥补了前者留下的缺憾。
推介:李兴华
编辑:潘天舒 王佳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