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k,Margaret. 2001. Twice Dead: Organ Transplantsand the Reinvention of Dea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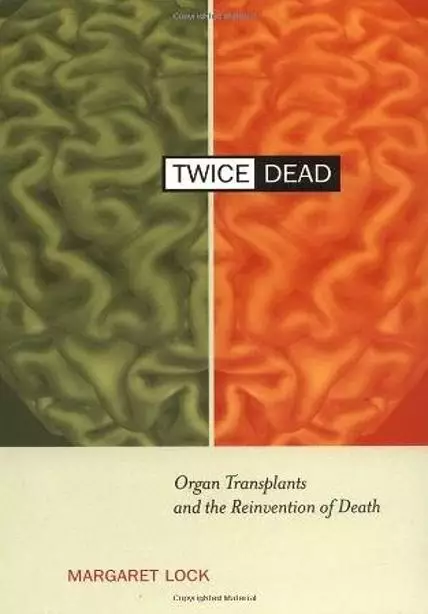
在这本民族志中,作者试图探讨,生物医学的科学和技术如何与文化互相纠缠,使人们建立起脑死亡与人类生命终结的假设之间的联系。作者的探讨触及了社会生活和人类生命的一些基本范畴,这些范畴往往以并列或对应的形式呈现,包括自然与文化、生命与死亡、自我与他人、人与身体,这些范畴看似具有本质性的指向和清晰的边界,但在生物医学、社会文化、市场等多方主体的推动下,这些范畴形成了纠缠和交互,生成了诸多新的混合实体。这些模棱两可、暧昧模糊的混合实体,在社会生活的秩序中对人们的观念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作者言说的重点。
在这一研究中,死亡如何被确定(locate),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同时包含了另一个问题:死亡应该被置于生物的、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层面去探讨?不论是生物医学领域还是社会文化领域,针对死亡所形成的知识,都是模糊的、处于变化中的,并持续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
生物科学自身的意向性就存在历史性的变化。在19世纪生物科学的形成阶段,人类开始对地球上的动物、植物进行系统性地检验和分类,试图对环境形成系统性地认识和把握。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系统性的科学知识的扩充以及应用性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试图改造并控制自然世界,并试图以生物科学来应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文化的指涉,两者之间形成越来越紧密的关联和交涉。在这种背景之下,生物医学对于死亡的知识构建是动态的。如果仅仅从静态的现代生物医学的认识论的角度而言,生和死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具有特定的科学规律,因此,关于死亡的知识具有本体性和独立性,不会受到社会环境和道德秩序的影响。这种理性化和客观化的观点似乎代表了生物医学的“精神气质”,自然与文化之间被构建出了不言自明的界限,死亡被赋予自然的属性,并被置于文化的范畴之外。然而,生物医学的知识论和实践并不是一个本质化的、静态的理念或实践准则,它是一种动态的生成性的结果。在具体的社会情境和多方主体的关系的纠缠和交涉中,生物医学所主导的关于死亡认定的知识,以及脑死亡者的器官移植的实践,都受到了市场和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模糊的、变化中的知识和实践。
死亡如何被“定位”于脑部,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过程。在西方生物医学史上,人们曾经认为,腐败是死亡的最终标志。直到19世纪,人们开始形成普遍的看法,即心脏和肺停止功能,便是死亡的标志。在这两种话语中,死亡的定位是模糊的且抽象的。当人们用“腐败”来定义死亡时,便留下了较大的文化阐释空间:“腐败”的含义可以被文化情境所影响,而关于“腐败”的感受和判断,则和个体直觉、知觉、经验等息息相关。而当人们将死亡和心脏和肺的功能的停止联系在一起,关于“生”和“死”的认定,则需要依赖于人的身体,而人的身体本身,便与文化情境存在着诸多的关联。只有当“人”的概念被明确地限定在大脑中,并以“意识”作为生命存在的标准,大脑的破坏才能等同于一个人的死亡,而当“人”的概念扩散到整个身体,甚至延伸到身体之外,大脑的破坏就难以被认为是死亡的象征。因而,将死亡定位于大脑而非身体,则是一种排除死亡鉴定过程中的文化因素的手段,从而减少科学事实的确立过程中所要面临的“模糊性”。
在欧美的生物医学实践中,脑死亡的鉴定同样存在争议,而鉴定标准的标准化和制度化并非是一个仅仅依靠生物医学的实验和归纳的过程,其间夹杂着多重主体的干涉和互动。民族志指出,1981年,美国已有6种脑死亡的鉴定标准,而出于器官移植的市场需要,人们需要建立一套标准化的死亡鉴定的公共政策。在人们的协商过程中,仅有不到一半的成员是医生,移植外科的医生也并未入席。人们最终所草拟的法案,需要得到美国医学会和律师协会的支持,最后才能被大多数州立机关通过。其中,美国医学会指涉日常的生物医学实践,而律师协会则需要通过一项确定的生物医学法规来确定器官移植过程中的权责,从而推动器官移植市场的确立和扩展。因而,在知识话语标准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中,生物医学仅仅是其中的仲裁者之一,制度性权力以及市场需求同样对知识话语的生成起到关键的作用,它们更有权力抹除一项生物医学事实中的模糊性,或是凸显其它的微弱的可能性。
在欧美的案例中,游走于生与死的界限的身体的商品化,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在民族志中,作者对尸体的商品化历史进行了梳理。早在19世纪,欧洲便已产生将尸体用作医学解剖用途的实践。然而,尸体的来源并不是完全合法或公开的,它们往往来自被处决的罪犯或是乞丐的尸体。因而,在早期的解剖医学实践中,人们便试图通过使用没有确定的社会身份或社会分类的人的尸体,来抹除尸体本身的文化因素的涉入。只有当尸体被抽离文化的情境,被剥夺社会意义,被客体化为价值无涉的生物对象,才能是一件可以被流通、估值的商品。
在作者的民族志文本中,存在诸多对于脑死亡患者器官摘取的直观描述。在这些描述中,被解剖的身体、依旧在跳动的器官、以及精准化的摘取,集中凸显了这一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人们无法明确定义被摘取器官的是一个“身体”还是一具“尸体”。呼吸器等医疗器械的介入,目的并不在于维持身体的生命机能,而是为了保证器官的新鲜。生物医学话语和技术实践共同制造了一种模糊的商品,这件商品游走于生与死、自然和文化的边缘,却始终不属于任何一方。
在作者看来,器官摘取和移植能在欧美形成市场,存在多重的原因。一方面,欧美社会具有特定的基督神学的社会思想基础,人们愿意相信“生命的礼物”(gift of life)的隐喻及其所隐含的互惠的意义,形成利他主义的社会倾向。另一方面,欧美社会具有普遍的功利主义社会思潮,注重事物的效用,并试图使大部分人收益。更为重要的是,欧美社会试图生成一种更有“意义”的死亡。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布满了可控或不可控的风险,意外的死亡代表了失控,人们无法抹平这些意外所带来的不安。因而,器官捐献似乎能使“毫无意义”的死亡变得更有价值,无名的死者变成了英雄。其中,生物医学技术则扮演了控制者的角色,以商品化的方式,重申了死亡所带来的互惠的可能。
然而,在作者所进行的比较研究中,日本社会对于死亡的鉴定标准以及器官移植实践则具有更多的犹豫和怀疑。在这一反差下,作者试图讨论文化在生物医学知识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作者的论述中,文化并非一个本质化的、静态的概念,文化依旧是一种生成中的、动态的实体。在日本社会中,文化是一种话语的政治,被用来表达不同群体的不同立场。对于普通人而言,死亡不仅仅意味着个体的消亡,它首先是一个家庭和社会事项。即使是医学上认定的死亡,也只有在家人接受的情况下才会成为最终的死亡。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存在亵渎尸体的禁忌,因而,文化的惯习使得日本民众对脑死亡的鉴定标准以及器官移植的实践持有怀疑和抵制的态度,而对于日本的文化评论者而言,这些阻碍生物医学实践的文化的惯习似乎需要被丢弃。同时,对于日本的生物医学专家及职业群体而言,他们接受的生物医学训练使他们更倾向于关注临床的器官移植需求。最后,对于国家的管理者而言,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的议题似乎成为话语的政治,成为重申民族主义认同的工具。由此可见,文化本身存在多元性和复杂性,它是一个多主体的生成实体,其中隐含着多重的关系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