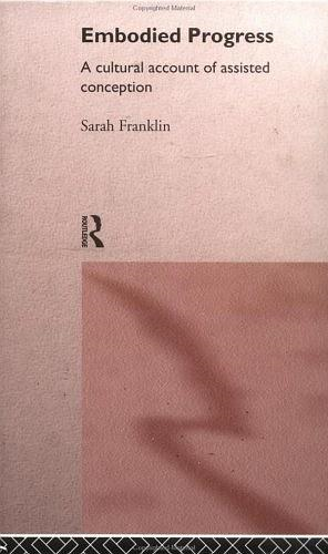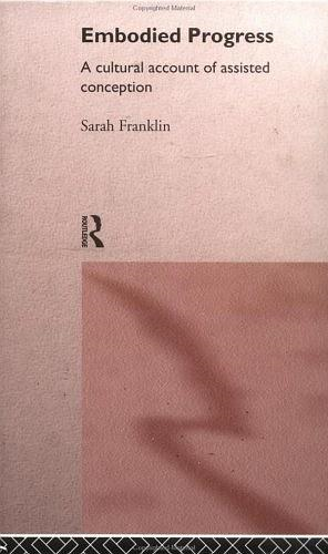Embodied progress: a cultural account of assisted conception
Sarah Frank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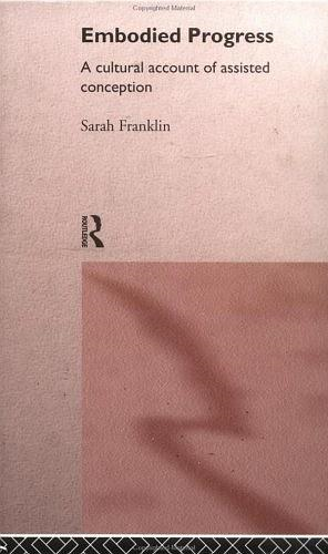
在这一民族志中,作者弗兰克林(Sarah Franklin)主要关注辅助生殖技术给社会带来的一系列的伦理和道德困境,包括亲属关系的重构,生育选择成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辅助生殖技术正在重构人们生成生命谱系的方式,而这项技术的复杂性、困难性和模糊性,重塑人们对于生育及其实践的认知。基于对女权主义人类学家的理论梳理,作者对性别不平等的生物决定论以及结构决定论进行了反思,最终倾向于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并非由生物性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历史性的因素构成的,当下语境中的女性从属地位是当下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以往的社会的残存。从这一论断中,作者反思了生物决定论和结构决定论中所隐含的本质主义倾向,强调性别关系生成的情境性。然而,在人类学既有的亲属制度研究中,人们往往基于生物决定论的视角来强调两性在生殖过程中的自然差异,并以此来构建性别关系、亲属组织以及血亲谱系的本质属性。诸多早期的人类学家认为,亲属关系是由血缘所决定的,父权只有通过生物学的定义才能显现。从19世纪末开始,能否“准确”地定位的亲子关系,是衡量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准。根据进化论的观点,野蛮和文明之间的区别正是通过对“生命事实”(the facts of life)的认识而被区分和排序,因而,对早期人类学家来说,父权的知识的明确与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息息相关。并且,人们对生命的形成、生殖的过程的知识建构,受到生物学理论的影响,因而强调生育过程中确定无疑的因果关系。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一些文化中,并没有绝对的生物性的亲子关系的认知,不仅存在生物性父权,同时也存在社会性父权。此后,英国社会人类学开始普遍接受这种由社会和自然因素构成的双重亲属关系模式。然而,马林诺夫斯基并没有体认到社会和自然因素之间的相互交涉和纠缠的关系。在20世纪晚期的人类学研究中,“生命事实”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话语,它从一个被假定为普遍的、不证自明的、确定的事实转变为一个动态的、模糊的、生成中的事实。简言之,人们对于生殖的话语和知识的理解历经了去本质化的过程。
在辅助生殖技术中,“辅助”是一个模糊的、流动的、生成性的概念。在作者的田野数据中,很多女性都清楚地意识到,试管受精的成功率比较低,即便怀孕了,也不一定能顺利产下孩子。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辅助生殖技术的副作用知之甚少,很少有人知道这项技术中使用的药物存在潜在的副作用,即便有人意识到副作用的存在,这些副作用也都被认为是最小的。同样,当被问及多胞胎的风险时,尽管人们很清楚这种可能性,但他们并没有表示出任何担忧,并且认为多胞胎是一种奖励。因而,辅助生殖技术的“辅助”意涵是模糊的,它并不是一种确定性的事实。然而,“辅助”的意义却是经由前来诊疗的女性的确认和制造的。这些女性具有一定的群体特征,她们往往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培训,消息灵通、见多识广、能言善辩,且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对自己的经历有深刻的反思。她们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功用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同时,她们对国民保健服务的生育治疗并不满意,她们更喜欢辅助生殖诊所提供的服务。因而,诸多女性选择辅助生殖技术,往往具有多重的原因,不仅在于她们自身的愿望和需求,也在于这些辅助生殖技术制造了一种“希望”的话语。在自我定位方面,辅助生殖技术强调整个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诊所将试管婴儿的步骤描述为简单且自然的过程:获取卵子、体外受精、植入胚胎,并强调这一过程和自然的受孕方式之间的一致性,并将这一技术描绘为“向自然伸出援助之手”(give nature a helping hand)。在这一话语中,“自然”这一概念具有多重含义,它不仅在宣称辅助生殖技术如同自然一般具有微妙的客观性,它同时也在强调这一技术的伦理的正当性:这一技术不论在形式还是本质方面都非常接近自然。在这一过程中,获取卵子、体外受精、植入胚胎这三个步骤被进行了本质化的处理,这些步骤可能遭遇的模糊、困难和风险被人为抹除了,这些步骤可能面临的文化困境也被刻意抹平了,最后呈现给患者的是一种被纯化(purification)过的话语。事实上,辅助生殖技术既包含了体内的技术步骤,也包含了体外的技术处理,这一部分的技术操作是独立于女性身体之外的,但诊所依然强调“技术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具有绝对的安全性。诊所往往会描述排卵的诱导过程,而不会描述试管受精的过程,而后者才是这一技术的核心步骤。因而,在整个过程中,辅助生殖技术被医疗机构通过话语的政治进行了有选择的“自然化”的处理,自然的生命事实被加以重申,技术以清晰的形式和模糊的本质,重新被嵌入自然的范畴。然而,生殖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完全受自然因素决定的过程,它同时包含了文化的影响,它是一种情境性的、生成性的并且需要女性去“体认”的事实,它和女性的意识和身体存在紧密的关联。而在辅助生殖技术中,文化的关联并没有被强调,技术本身可能带来的文化风险也被并未被提及。
许多参与辅助生殖技术的女性将这一过程比喻为“障碍赛跑”,这代表了一种经过“体认”的事实。在辅助生殖的过程中,女性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配合这项技术,并且需要经历层层的技术步骤才有可能通向希望的“终点”,而每一个步骤都存在失败的风险。女性需要去体认这些层层的风险,并且最终相信,失败是“正常”的,每一个辅助周期都有可能因为其中的一个风险或缺陷而被“丢弃”。如果女性接受了这一事实,那么,这一过程中任何一个跨越了“障碍”的步骤都意味着“成功”,即便最终并未达到辅助生殖的目的,也能给女性带来“过程的胜利”。我们可以看到,辅助生殖技术将生殖过程进行了碎片化、切割式的处理,生育不再是一个连贯的体认的过程,它被客观化为分散的、局部的阶段,每个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模糊性和风险性,女性需要像攻克障碍赛跑一般,去体认这一不连贯的过程,并承担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控制了一切,女性如何生成主体性的生育认知和体悟呢?伴随着对辅助生殖技术过程的“接管”,女性需要建立一整套生活方式去配合这项技术,并对这项技术所制造的希望有所期待。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被客体化了,技术支配了原本该由她们进行主体性的体认和生成的过程。辅助生殖技术以模糊的本质、“自然”的外衣,以另一种方式强调了生育背后的性别秩序。在制造希望的话语之下,生殖困难的女性似乎“不得不”去尝试这一项技术,这些看似“不得不”的决定背后,依然是强大的性别秩序的话语政治,以及这些政治在技术中的隐蔽化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