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Cohen, Talia. Tracing complexity: The case of archae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22.4 (2020): 733-744.
本文作者Talia Dan-Cohen为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人类学副教授,其研究和教学探索人类学、历史和科学哲学之间的交叉点。她感兴趣的领域包括生物技术、知识实践、社会科学史和当代社会理论。

20世纪80年代,“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作为一个高度跨学科的研究项目,开始吸引各领域科学家的注意。复杂性科学旨在阐述复杂系统的抽象原理,汇集了众多领域的知识和实践。物理、经济、理论生物、计算机、数学、哲学、语言学、人类社会,所有这些都被这一个共同的主题收拢到一起。作为“复杂社会”和“社会复杂性”的历史出现问题的代表,考古学家们一直参与其中。
而在考古学科内部,对复杂性的讨论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大部分含义来自于19世纪的进化思维,在20世纪中叶伴随新进化论而复兴。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复杂性都是一个热点议题,随着考古学、人类学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实践的变化,学者们在不断辩论、定义和重新定义、反对、解构和复兴复杂性,围绕这一术语产生了规模庞大的文献库。
作者在本篇文章中梳理了考古学中“复杂性”概念的扩张过程。并非对全部文献进行综述,而是将之作为一个人类学主题来看待,考虑复杂性概念和用途背后潜在逻辑的动态变化过程,视之为不同美学、政治和道德思潮的历史载体。
复杂性与复杂性科学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复杂性的概念被引入到截然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项目中。一方面,对于一些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学者来说,复杂性成为他们寻求科学大一统和争取技术科学霸权的主要术语。1988年,著名物理学家海因茨-帕格尔斯(Heinz Pagels)写道,“我相信掌握了复杂性新科学的国家和人民将成为下个世纪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对一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来说,复杂性也成为提供了抵制还原论和简化(reductions and simplifications)的工具。在1988年的文章《情境知识》中,唐娜·哈拉韦(Donna Haraway)借用阿尔都塞的观点,认为“女性主义的客观性在最后一刻抵制简化”,强调女性主义的不可还原性和复杂性。因此,复杂性同时被标榜为现代技术科学、统一主义和普遍主义抱负的概念,又反过来并被作为一种明确拒绝这些抱负的概念。重要的是,在这两个框架中,复杂性通常都被视为一件好事。

考古学的特殊之处在于,上述两个框架在此处产生重叠。文化人类学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旗帜鲜明地反对实证主义,早已放弃加入“可靠科学俱乐部”,但作为其近亲的考古学中科学和人文两条路径一直共存。在考古学中,复杂性议题本身就是在与不同的理论范式的交互中诞生,包括进化论和新进化论(evolutionary and neoevolutionary theory)、马克思主义(Marxism)、系统论(systems-theoretic approaches)、热力学(thermodynamics)、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adaptive-systems theory)等等。与此同时,在人文一侧,考古学家跟上了女权主义和后殖民批判的脚步,对复杂性研究中的还原主义因素抱有疑虑。考古学家长期以来一直采取干预措施,希望消除欧洲中心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的滤镜。然而,这些关键的干预并不意味着放弃这个术语,而是重新定义和不断扩充这一概念。考古学的众多重要主题都涉及到对复杂性的讨论,包括社会演化、复杂狩猎采集群体、永居和农业发展、崩溃(collapse)、韧性(resilience)、合作和集体行动(cooper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社会变化与人与自然交互模型、自组织的出现(self-organization and emergence)、行动者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等等。
复杂性的演化
复杂性概念最初来自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著作。1857年,斯宾塞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设: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顺序是进步的本质,即一种从同质状态到异质状态的变化。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在他的考察范围内,在他看来,政府组织、宗教组织、风俗和礼仪等等社会要素都沿着一条从简单到复杂的路径发展,也就是说,从同质到异质。
20世纪初,在博厄斯学派的文化相对主义影响下,社会进化论被美国人类学界短暂地拒绝了一段时间。但在世纪中叶,进化论思维融汇于一批全新的考古学理论之中,在北美考古学界东山再起。新进化论思想的一个直接源头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文化演化是一个渐进的压力-适应的辨证过程,制造了一种有序序列。当时有很大影响力的考古学家,如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和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历史哲学运用到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框架中。莱斯利·怀特和他的学生们关注斯宾塞对于从同质到异质的区分,将其重新定义为热力学问题,用能量来描述和衡量社会的变化。怀特的追随者之一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继续在这一方向上进行讨论,以能量利用方式来确定社会进步的水平——能量越集中于结构、结构越复杂,可以利用的能量就越多。一个系统如果各部分更专业化,并且整体更有效地集成在一起,就能达到更高的“整合水平”,这在新进化论范式中被作为一种比较单位,某一社会可以根据其相关特征被置于一种社会类型学序列中。进步的特征包括物质要素的扩散、劳动分工的增加、社会群体多元化,以及特殊整合手段的出现——政治(如酋邦和国家)和哲学(如普遍的和道德的宗教和科学)。沿着这一路径,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提出的著名社会序列——游团、部落、酋邦、古国和民族国家——成为一整代人类学家的分类坐标。六十年代,过程考古学,或称为“新考古学”范式兴起并迅速占领北美考古学界,对复杂性和复杂社会的关注继续延续下来,并与系统论结合在一起。这一阶段不断有学者试图对复杂性进行定义和完善。
到了八十年代早期,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拒绝进化逻辑,新进化论考古学以及它所依据的历史哲学受到了直接的攻击。社会科学的整体转向,加上女权主义和后殖民批判,对复杂性议题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复杂性的扩张
随着学科实践的积累,考古学家们对各类型社会的认知都在加深。许多原本被贴上“简单”标签的社会也显示出其“复杂”的一面——狩猎采集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起初,狩猎采集社会被认为是均质、平等、小规模的简单社会,而复杂社会一般在农业和定居出现之后才有机会发展起来。然而狩猎采集者的这种经典形象在七八十年代被逐渐重塑。例如1981年道格拉斯·普莱斯(T. Douglas Price)的《非复杂社会的复杂性》(Complexity in Non-Complex Societies)一文,尝试在狩猎采集者中识别社会复杂性。这类主张修订了社会复杂性出现的时间表,以及拒绝了复杂性-农业的绝对关联。需要明确的是,普莱斯的贡献并非旨在切断复杂性与社会进化论之间的联系,而是把复杂性考察范围扩张到进化序列的更早环节。
复杂性的概念不止在狩猎采集者这一专题上得到扩展。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理论范式开始将社会复杂性问题视为一个连续体,拒绝此前“复杂/非复杂”的二元切分。作者在社会崩溃研究中观察到了这种转向。1988年,在《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中,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Tainter)将崩溃定义为复杂性的突然丧失,此处的复杂性被理解为一种连续的阶梯式的指数。崩溃会发生在任何社会中,复杂性也或多或少存在于所有社会中。这也意味着,社会复杂性不是那种可以确定其起源的现象,任何社会中复杂性可以增加或降低,但不存在某个复杂性开始出现的社会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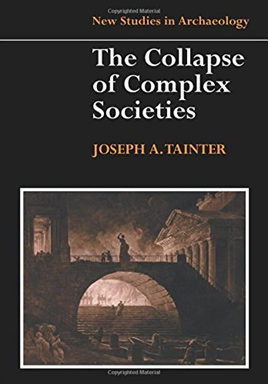
复杂性的批判
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类学开始流行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批判,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这一关键转折也无疑波及到了考古学。1989年出版的《支配与抵抗》(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文集是这一方向的典型作品,由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迈克尔·罗兰兹(Michael Rowlands)和克里斯托弗·蒂利(Christopher Tilley)共同编辑。在引言中,他们指出,考古学中对复杂性的主要研究方法涉及形式的、数学的、抽象的模型,人们可以将考古发现与之进行比较。然而在这种研究路径下,尽管模型足够精巧,但其与真实考古世界之间还是存在巨大鸿沟。当尝试连接二者时,总是不可避免地重复原始主义和一般进化论的思维。这些深受阿尔都塞、葛兰西、福柯和布迪厄影响的考古学家提出了另一种复杂性研究路径,以“社会异质性”(heterogeneity)作为抓手,思考不平等、支配和抵抗。然而,在普适法则、实证和情境化、阐释的对立立场上,这些学者似乎显得模棱两可。一方面主张选择更具体的“支配与抵抗”形式作为重点,对所有形式的社会复杂性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又提出有必要对复杂性进行重新情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即所使用的概念结构将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而被赋予新的内容。

后殖民批判的印记在整本文集中都很明确。在这本书的另一章中,迈克尔·罗兰兹尖锐地指出,考古学界对复杂性的建构是在一种西方中心式的意识形态下完成的,其历史背景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复杂化的顶点指向一种包罗万象的大都市。然而,罗兰兹承认,就算是如今对复杂性批判仍然是世界格局变化下的新型支配战略产物——强调激进的异质性和文化差异实际上更符合工业化的第三世界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精英们的目标,他们寻求自治和身份认同,以便掩盖和迷惑他们自己权力的来源。
不管怎样,七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考古学家们陆续拆除了新进化论范式下对复杂社会演变序列的各种刻板印象。例如:不平等和异质性之间存在区别;就算是在所谓的平等社会中也能找到基于性别和年龄的不平等;不平等不一定与农业强化捆绑;财富不平等可以与政治不平等分离,等等。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推翻复杂性,而是为了指出导致其被滥用导致的错误偏见。
另外,也有学者开始关注“简单性”(simplicity)。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认为,考古学家几乎只关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创新和复杂性,而忽略了生活中那些被简化的方面,比如日常消费。社会生活在不同方向上分别走向复杂化和简化,二者均应受到重视。
折叠复杂性
对复杂性的另一种重塑涉及到对以往所谓“简单社会”的复杂性考察。此举与一些复杂狩猎采集社会研究具有相同的形式特征,但对进化问题的强调可能较少。苏珊-阿尔特(Susan Alt)在2010年主编的《古代复杂性》(Ancient Complexities)文集的序言中质疑了考古学家评估北美前哥伦布时代社会复杂性的方式。她指出以往认定社会复杂性的标志,如宫殿和皇家陵墓,实际上暗示着以一种“像我们一样”的方式复杂。以一种更倾向阐释和人文的视角,阿尔特认为复杂性应该在“一个社会的特定历史和细节”中寻找。这一主张使得复杂性成为一个体量庞大的分析问题,没有什么社会是无法进行复杂性分析的。正如本书最后一章中诺曼·约菲(Norman Yoffee)所言,为了看到史前北美人是如何以复杂的方式行动,互动和理解他们的生活,考古学家需要放弃“复杂性”(作为一个具体化的,必要化的,可识别的社会实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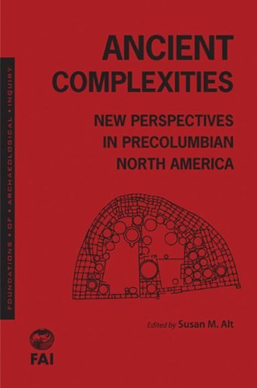
用复杂性理论弥合分歧
大约在《支配与抵抗》出版的同时,在考古学科之外,复杂性科学获得了突出的地位。学者们为巩固对复杂性的理解而进行跨学科努力,为考古学注入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工具,用于思考和建模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例如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和非线性动力学(nonlinear dynamics)对人类社会性的内在复杂性的探索,以及对复杂性理论建模工具的利用。
此时,复杂理论与更早时过程考古学派的系统论存在区别。考古学系统论将社会定义为在适应状态和平衡状态之间移动的动态系统,而复杂性理论将社会定义为开放的非平衡系统。这些新方法被认为有希望能弥合以往的两种研究范式的极端分歧:要么以过度简单化的形式追求普适的“人类行为法则”,要么追求极端的情境主义。McGlade和van der Leeuw指出,非线性动力学的见解构成了一个关键的中间点,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工具,支持用正式的和相对简单的术语描述非经常性的、不稳定的和不可预测的现象。这个框架包含了20世纪80年代在复杂科学标志下重生的统一主义梦想,远远超出了考古学的范围,涵盖了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之间以及科学本身之间的鸿沟。这一梦想在考古学和其他领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
复旦文博与考古系 赵潇涵 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