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rth, L. M. (2001). Is the “World Game” an “Ethnic Game” or an “Aussie Game”? Narrating the Nation in Australian Soccer. American Ethnologist, 28(2), 363–387. https://doi.org/10.1525/ae.2001.28.2.363
前言:本周推荐的文章出自美国文化人类学者Loring Danforth。他于20世纪7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人类学训练,受教于格尔兹的他同样致力于诠释不同文化中的各种象征性、表达性符号。他的早年研究兴趣为现代希腊宗教仪式与灵性生活。后来因为在一次探讨会与希腊民族主义分子在马其顿问题上的立场发生冲突,Danforth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种族与民族身份的建构、民族主义以及人权问题。
作为他后期转向的代表作之一,此文以足球为棱镜,通过梳理澳大利亚的足球发展历史,映射出澳大利亚在民族主义叙事方面的紧张与矛盾,并与霍米·巴巴的研究进行了对话。他意在指出,正是澳大利亚国族叙事的矛盾心理(ambivalence)以及国族叙事的能量,使得澳大利亚足球中的各类行动者能够操演不同版本的澳大利亚国族叙事并为自身的利益服务。同时,作者也希望借此文说明叙事在身份构建中发挥的作用。(本次推送的封面图是澳大利亚传奇球星、前澳大利亚国家队队长蒂姆·卡希尔,他曾经短暂效力我国上海申花队和杭州绿城队。有趣的是,他的母亲为萨摩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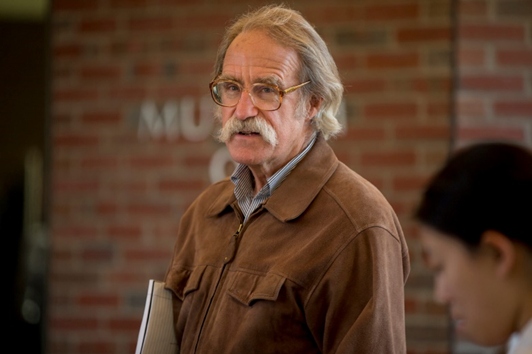
Loring Danforth. Photo byPhyllis Graeber Jensen/Bates College.
一、霍米·巴巴的国族叙事及其拓展
Danforth在文章开篇介绍了霍米·巴巴的著作《国族与叙事》。在这本书中的导论部分,霍米·巴巴探究了“叙述国族”这一概念。在叙述的过程中,人们协调自身与国族的关系。霍米·巴巴关注以叙事形式表达的国族(nation),他邀请读者探究不同的叙事方式,考察人们如何编排国族叙事的桥段(Bhabha,1990:3)。
霍米·巴巴以文学文本作为研究国族叙事的起点,关注文本中对于国族的描绘以及民族主义的文学化表达。而Danforth认为,体育运动也是一种叙述国族的方式,体育运动和文学在“想象”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都发挥重要作用。它们都作为表达国族身份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中介,并为与国族生活相联系的意义与象征领域的建构提供了机会(Bhabha,1990:3)
霍米·巴巴在其著作中还提到,国族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具有矛盾心理(ambivalence)。语义滑动(semantic slippage)则使得意义从一种叙事转移到另一种。而在国族叙事过程中也存在着国族统一性的问题。此外,霍米·巴巴认为国族的矛盾心理(ambivalence)萦绕于有关国族的观念(Bhabha,1990:1)。以上提及的叙事矛盾性、语义滑动性和国族统一性问题,实际上向我们表明,国族叙事并非一成不变,它是变化的、流动的,有时会出现多种叙事共存并且自相矛盾之处。
基于以上的理论视野以及现实考察,Danforth认为澳大利亚的足球历史彰显三种不同的国族叙事版本,同时,澳大利亚的社会状况也使得其叙事很好地体现出国家在民族主义叙事方面的矛盾心理。因此,Danforth以澳大利亚的足球运动为棱镜,展示足球如何作为一种叙事方式,表达澳大利亚社会当中存在的三重叙事以及矛盾心理。
二、澳大利亚的三重国族叙事:一统、多元与杂糅
1788年1月26日,英国海军上将亚瑟·菲利普率领首批移民抵达悉尼湾,并在此建立罪犯流放地,后来这一天被定为澳大利亚国庆日。但200年过去,澳大利亚人并没有就传统的国庆日达成共识。而自1901年成立联邦以来,澳大利亚人就以不同版本的国族叙事诉说自己的故事。不过直到20世纪末,这些叙事尚未达成一致。
究竟什么才是澳大利亚?谁才是澳大利亚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推动与世界市场的加速整合之下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种族构成的复杂性以及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承诺,也迫使澳大利亚在建构民族身份时不得不考虑种族多元性的问题。国际环境使得民族国家边界逐渐模糊,社会内部又趋于多元化。在这种“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澳大利亚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叙事。
首先是“传统版”叙事。这个版本强调澳大利亚人的盎格鲁起源,以说英语的白人为主体。这种叙事实际上是对其宗主国的追随。
第二种叙事是“多元文化”叙事。这个版本伴随着二战以后兴起的移民浪潮而来。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废除了一度盛行的“白澳”政策,转向多元文化主义。这种叙事强调尊重不同族群的语言、文化并保障其权益。但这种取向背后的意图是明显的:把澳大利亚维持在一个整体的范畴内,在多元中谋求一统。然而这种叙事如作者所言:“澳大利亚的文化多元主义的目标是虚弱且肤浅的,它仍然在建构一种同质化的、合成的并且是欧洲化的民族身份”(Danforth,2001:369)。
第三种叙事是“文化杂糅”。它脱胎于多元文化叙事,强调文化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而不强调同质性和大一统。它意味着杂糅的各个部分保留各自的传统,各有其独特起源。这是一种更为极端的叙事方式。霍米·巴巴认为,杂糅(hybrid)构成了不可比较的要素以及无法被同化的顽固肌瘤(Bhabha,1994:219)。文化杂糅使得身份(identity)总是处在被建构的过程中。也正因如此,杂糅(Hybridity)矫正了那种民族身份与文化的本质主义观念(Pieterse,1995:55)。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杂糅是对前两种叙事的超越,因为不同的文化要素不断进行结合与再结合,占主导的文化也总是处在开放和再次复兴的状态当中(Danforth,2001:369)。
三、作为叙事工具的足球
Danforth以澳大利亚不同时期的足球生态描绘三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叙事,进而体现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叙事中的矛盾心理(ambivalence)。而这种矛盾也使得不同利益主体能够运用不同叙事策略以达成自己的政治或经济目标。
最初,英式足球(soccer)被视作一种“种族竞赛”(ethnic game)。它不是澳大利亚主流的足球形式,但随着移民浪潮,英式足球逐渐得到发展。不同种族的人们组建了根植于当地社群的俱乐部。这种富有种族色彩的球队代表着特定的身份,在面对同化压力和培育团结性时发挥重要作用。在特殊时期(比如不同族群的母国发生政治冲突),足球场上的较量更是成为一场“代理人战争”。卷入其中的球迷、球员以及社群领导人以足球竞赛、谩骂、暴力冲突的方式表达政治诉求并谋取政治利益。
在这个意义上,足球作为“多元文化”的叙事方式,以足球比赛和各种与足球有关的文化元素(队歌、队旗、球衣)团结了特定族群的个体,塑造了强烈的认同标志。社群领导乐于利用这种叙事以促进自身政治利益。然而,小群体的高度团结很可能与更大范围内的统一相冲突。
到了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足球事业的官员出于经济动机而意欲推动足球发展。其中一大举措就是足球的去种族化。一个名叫David Hills的官员推出了许多具体措施,比如要求某些球队改名,队名不能含有种族色彩。而那些富有象征意义的队歌、球衣、旗帜也同样遭到禁止。毫无意外,这种做法遭到了球迷和社群领导者的抵制。
到了98年的法兰西之夏,澳大利亚开始将国家足球队打造成含有一统(unity)暗示的身份认同标志。追随国家队使得来自不同族群的球迷暂时忘却彼此的文化差异,一起为澳大利亚(队)呐喊。实际上,这是澳大利亚应对世界经济体系扩张、民族国家边界被全球化带来的商品化、美国化冲破而做出的回应。外来赞助商的冠名权及其商品的推广(比如可口可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威胁到了澳大利亚的民族叙事。
面对这种“国将不国”的局面,澳大利亚有必要采取一种单一的民族主义叙事,让多元汇聚成一统。因此,澳大利亚国家足球队被塑造成极具国民认同度的符号,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Danforth认为,澳大利亚的这种单一叙事是一种传统叙事。它看似去种族化、“澳大利亚化”,实则是“盎格鲁化”。这不难理解,澳大利亚的政治权力实际上掌握在盎格鲁血统的白人群体手中,他们的去种族化并不意味着在进行叙事时没有参考模板,而他们作为“主体民族”,自然会将澳大利亚民族塑造成自己的样子。但这种做法又有违政治层面上对社会多元性的承认,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单一叙事与多元文化的叙事共存的局面。
作为多元文化的个体,他得以保留自身的传统习惯、生活方式。但这种多元文化的表达被限制在了私人领域。少数族裔挥舞国旗支持国家队的行为是受到鼓励的,但如果挥舞自己社群的旗帜则会受到批评。多元文化叙事被框定在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只允许作为统一整体的澳大利亚的存在。这种叙事在Danforth看来,未免过于肤浅。当然,这也很好地体现了民族叙事中的矛盾心理:既要统一,又要多元。
随着这种矛盾叙事的发展,杂糅文化叙事出现在了澳大利亚足球当中。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俱乐部开始走上合并、更名的道路。比如South Melbourne Hellas更名为South Melbourne Laker。前者具有明显的希腊色彩,而后者则显得更为美国化、大众化。在官方的、对外的场合,球队以“Laker”的面貌示人,意在吸引更多观众。而在具体的足球比赛中,球迷以及他们使用的各种文化符号(呐喊口号、旗帜)则保留了“Hellas”这一希腊特色。
这种杂糅的做法在Danforth看来面临一种张力。在Laker-Hellas的复合名称中,左端具有向心力(单一叙事的传统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右边具有离心力(多元文化叙事)。两种力量的拉锯,使得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叙事始终处在一个变动的过程。
总之,足球作为一种叙事工具,跟随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面貌。
四、结论与思考
Danforth通过翔实的材料和精细的论证表明,足球运动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体现了澳大利亚在构建国族叙事时的矛盾心理与多重面向。在这个意义上,Danforth拓展了霍米·巴巴理论的应用范围。除了文学,其他文化载体同样能够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向我们建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4年前,为了提高打进世界杯正赛的几率,中国足协开始运作数名南美球员归化入籍,这种做法在当时遭到了一些非议。有球迷认为,归化球员的加入,使得中国队不再是中国队。在足球战绩与民族情感之间,归化球员的处境稍显尴尬。

图:新华社。2021年11月16日,在阿联酋沙迦举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B组第六轮比赛中,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图为中国队首发球员赛前合影。

2001年,沈阳市五里河体育场外,国足踢进世界杯后,球迷疯狂庆祝,高呼祖国的强大(图源:人民视觉)
正因人类具有根据外部情势而做出策略性反应的能力,作为一种叙事工具的澳大利亚足球才会演化出不同的版本以适应新情形。窃以为格尔兹口中的意义之网兜住了人类,使其不再向虚无下坠。那么,作为观察者,当我们看见一个文化现象随时间变迁,除了描述它的变化,更要试着理解,这种变化对生活带来什么意义?象征了什么?背后又折射出什么更大的社会历史变迁?我想这篇文章为我们的观察与诠释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参考文献:
Bhabha, H. K. (1990). Introduction: narrating the nation. InNation and narration (pp. 1-7). Routledge.
Bhabha, H. K. (1994).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Danforth, L. M. (2001). is the world game an ethnic game or an Aussie game? narrating the nation in Australian soccer.American Ethnologist, 28(2), 363-387.
Pieterse, J. N. (1995). 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Global modernities, 2, 45-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