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kling, Robert. Expression and generalization i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American Ethnologist 2.2 (1975): 239-250.
本文发表于1975年,作者Robert Conkling当时为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生。文章是对当时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的回应——历史和社会领域是否存在规律和通则(lawsor regularities)?是否需要使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如果不用科学方法,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是如何认识事物的?本文作者试图说明,对于社会进程的历史和人类学知识来说,严格的科学主义方法是没有必要的,并将对几位人类学家的研究和实践进行对比和评估。
书写历史:认知、交流和叙事
作者首先引用历史学家杰克-海克斯特(Jack H. Hexter)的观点,总结了人文研究中语言风格和写作逻辑的重要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必要性,引出唤起性语言、叙事和修辞的概念。
海克斯特将不同学术领域的知识表达区分为“指称性的(denotative)”和“唤起性(evocative)”的。这源于不同学术实践中,认知和书面交流之间的差距。物理学家或化学家的科学词汇是精确的、量化的、指称性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知识本来就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而历史学家面对的知识融合了一些与行动和情感相关的体验,人很难用指称性的术语来陈述这些经验。于是,为了充分呈现这些经验式见解,他们有时会倾向于选择修辞性的、不精确的、可能模棱两可的术语和短语、格言和隐喻,以其丰富的内涵而制造“唤起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学家的体验是在另一个时空展开的。那么,问题就不仅仅是体验的交流,而是他们的体验与读者(历史学家自己)不熟悉的概念和规范的交流——这实际上构成一种翻译。此时唤起性语言有时恰恰是跨越认知和书面交流之间差距的最佳手段。
叙事(narratives)是对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的恰当回答,这些问题的性质类似于“事情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恰当的回答往往是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回答某种一般规律(general laws)。不过,一般规律的解释也可以嫁接到叙事之中,在这些叙事中连续因果关系把事件串联在一起,这种归因意味着找出一般法则的可能性。但问题是,因果联系或规律不能解释每一个事件,在解释的时间跨度、规模和节奏等方面,只有结合修辞性(rhetorical)或审美性(aesthetic)的回答,才能真正给出合适的历史见解。海克斯特认为,面对历史数据时,学者应当将分析和叙事结合起来开展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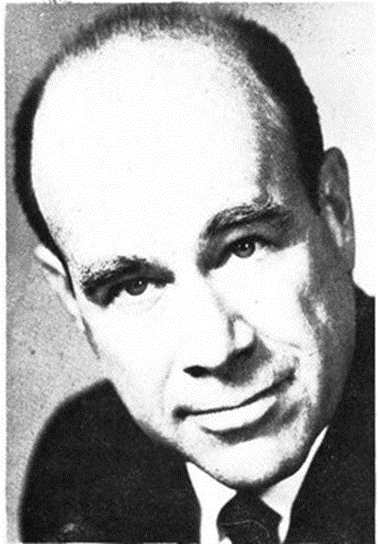
Jack H. Hexter
叙事、变化和规律
作者在本节主要讨论了人类学家迈克尔-加菲尔德-史密斯(Michael Garfield Smith)对客观性和通用规律的追求。这些探索并未取得让人信服的结果,作者试图以此为例说明人类学没有必要采取严格的科学主义方法。
史密斯在其1960年的著作中指出,在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对变化的研究,有必要使用历史方法(history)和叙事方法(narrative)。他呼吁人类学家使用叙事方法,因为它最适合处理那些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关系——正是人类学家需要重点对付的。历史和社会形成的两个关键特征——独特性和偶然性——进一步成为史密斯主张叙事方法的理由。叙事也对历史上的事故给予了适当的重视,强调了历史上的意外会如何影响发展。史密斯是一个向往科学主义、试图发现变化规律的学者,然而,他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蕴含一些修辞或审美上的判断,影响叙事的设计,包括起止、尺度、节奏等。不管怎样,史密斯尝试对历史数据展开分析,试图发现涵盖在叙事中的规律。他提出的“人类学的历史方法”与“历史学家的方法”不同,后者强调偶然性和独特性,而前者试图分析变化的过程本身。史密斯把这种方法用在了对扎佐(Zazzau)政府的研究上。“过程”(process)一词是此处的关键。其中暗含的推理逻辑是:假设各种变化形成了一个系统,并强调系统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不仅在扎佐,而且在任意假设存在“变化系统”的地方都是有效的。似乎变化存在一个本质,即变化的“过程”,史密斯想抓住这一核心。
然而,作者指出,史密斯努力发现规律、揭示变化过程本身时,他把变化当作了一种具有本质的事物,已经进入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立场。过程向前发展,不是由于人类的动机和行动,而是由于变化的“秩序”,它像一台机器一样,运作着历史。史密斯希望能发现像这样支配一系列事件的规律。作者认为,史密斯的努力是徒劳的,不管是偶然现象还是重复性现象,其规律都没有被证明是确实存在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任何现象都是作为以前独特事件的结果,而法则在每次应用时都需要相同的初始条件。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学家如何为自己和读者呈现自己知道的东西?如何书写社会行为?除了通过叙事,还可以通过什么形式来了解和表达?
人类学书写:翻译、客观性和模式方法
人类学研究应该以怎样的语言风格书写?作者将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作为一个样板案例,来讨论客观性问题。作为对比,史密斯的叙述中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唤起性的术语,完全以指称的方式来书写;而格尔茨在写作时会使用大量带有感情色彩的比喻、联想。作者认为,就民族志书写而言,格尔茨的方式更合适。因为民族志的客观性问题涉及到“翻译”,格尔茨必须努力使不同社会和文化的读者能够理解爪哇社会中的概念和价值。故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一样,有时必须使用唤起性的语汇,作者认为这样的表达并没有减损客观性,反而能够更好地呈现丰富的社会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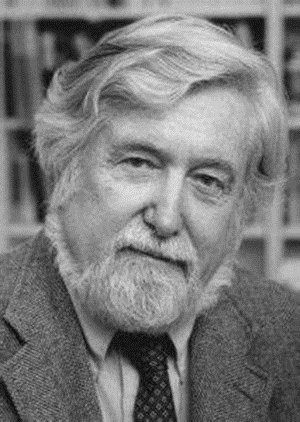
Clifford Geertz
那么,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通过社会科学而不是被观察的行动者提供的概念和价值来看待事件?作者指出,某个事件的意义,以及事件本身均是由行动者自己构建的。作者引用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的话,指出如果没有行动者的主观意向,外部观察者甚至无法知道某一行为的起止,甚至不能知道它是否构成一个行动。行动者的行为本身也正是基于这种对现实的定义和构建,这种零碎而模糊的社会现实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观察者应当将行动者的构建与他自己的观察结合起来,完成对真实事件的叙述。于是,“客观”(objective)不能仅指向不带情感的指称性术语和量化分析,它还意味着从观察者和行为人对事件的感知角度来描述事件,并为此使用必要的唤起性语言进行描述。民族志书写,也就是翻译的过程需要从观察者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行为者的文化,这就意味着对同一事件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那么,对于同一行为,若价值取向越多,分析便可以越丰富,能够促进知识的增长。
作者强调,他并不认为普遍原理在社会科学中毫无用处,重点在于,普遍原理应该以什么形式得到。作者在此讨论了“模式”(pattern)对历史和社会研究的意义。模式概念首先由克罗伯(A.L. Kroeber)提出,模式不是决定性的规律,而是相对确定的思考和行事方式。这个概念既包含社会科学家的通用化原则,也包含行动者的自主行动。作者用雕塑家来举例,雕塑家的创作受到石料性质和时兴艺术样式的限制,于是雕塑家的作品在该框架内呈现一种模式,没有人能事先精确地预测一件雕塑是什么样子。模式的关键在于设定发生变化的框架——这是一种适合历史研究的通用化(generalization)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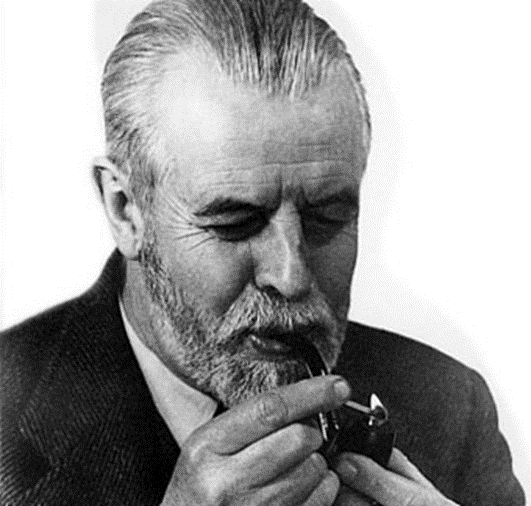
A.L. Kroeber
格尔茨便是通过“模式”这一形式来发现、整理和表达自己的认识。他对印度尼西亚城镇的讨论中提到“城市模式”、“农村模式”等等。面对某一特定社会现象和事件,大多数定量研究会将其作为某一种模式的指标;民族学工作视之为这种模式本身的内容;而在格尔茨的方法中,现象和事件可以被解释为模式的一种独特的、特别有说服力的现实化——它的缩影。研究者对行为的特征进行抽象化和选择,以展示他认为自己看到的模式,将模式与行为相匹配。在这种方式下,重复的和独特的事件都被纳入形式分析范围,社会行为不是随机的,但也不是完全被法则和规律所决定。通过运用模式方法,就有可能对社会行为进行归纳和比较。
结语
本文通过讨论两位人类学家的实践,尝试探讨几个大问题。作者认为人类学中没有必要使用严格的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方法。他指出,修辞或审美判断广泛存在于叙事的使用中;唤起性的,而不仅仅是表示性的语言,有助于更客观地了解发生在异文化中的事件;模式,而不是规律,是对事件的独特序列进行概括的最佳手段。一系列关于叙事起止、范畴和节奏的修辞性判断,加上唤起性的语汇、叙事形式和模式方法,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有助于扩展人类学家的认知范围。相反,如果在历史和人类学中只采用严格的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逻辑,将会严重阻碍学者们更广泛地获取社会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