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ns-Pritchard E E.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1
前言:本次推荐的文章来自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在曼彻斯特大学发表题为“人类学与历史学”(Anthropology and history)。作者探讨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通过阐明人类学研究忽视历史的后果,以及两者的区别,展示了历史之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应当将功能主义的共时性路径与历史学的历时性路径相结合”的观点,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Evans-Pritchard
一
在作者所处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先师马利诺斯基(Malinowski)和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依然对于英国人类学仍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作者认为,前两位大家对历史都抱有敌意(both extremely hostile to history),而即便其他学者没有敌意,也是持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至于邻国大师涂尔干呢?作者认为他的研究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基于这样的现状,当时的功能主义者对历史持一种批评与忽视的态度。为何功能主义者持这样的态度?这大概要从前人的研究说起。功能主义者认为,进化论与传播论流派的学者企图通过对不同社会的研究,找出能够描绘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规律。而在功能主义者看来,历史学是一种特殊科学(particularizing sciences)。与之相对,人类学被划入自然科学一类的普遍科学(generalizing sciences)。通过一些个案研究而总结出来的发展规律,是否真的能称之为普遍?在功能主义者看来,这些研究显然是不加批判的、教条的。他们这种对历史的态度,大概也受到后人对种族中心主义的批判的影响。
功能主义者的批评不无道理。但作者认为,功能主义者应当指责的是——他们写了糟糕的历史(bad history)——而不是指责他们写了历史。进一步地,Evans-Pritchard指出要区分历史的类型。他所指的历史,不是叙事性的历史,也不是历史哲学,而是一种具有社会学性质的历史学(historians-sociologues)。这种历史关注社会制度、社会运动和文化变迁,目的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挖掘一些规律、趋势、类型等等。比如马克思,韦伯等人,通过对封建制度、资本主义、阶级、革命等内容的研究,他们抽象出一些模型或理想类型。这些普遍性事实的背后,不正是功能主义者欲求的“普遍科学”吗?通过对历史进行一番社会学式的考察,我们得以找出一些恒久不变的事实或人类情感。
二
在回应了功能主义者对历史的批评以后,作者又进一步地指出人类学研究忽视历史的后果。比如,他认为一些学者(如涂尔干,弗雷泽)对文献资料不加批判的利用,这并不满足历史方法的要求。如果对文献资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缺乏考量,结论的根基也会随之动摇。
又比如,他认为一些学者没有试着从历史记录或者口头传统中重构过去人们的生活。缺乏对他者过往生活的了解,会导致一种二元分割的视角:把欧洲之外的(特别是殖民时代以前的)他者的生活看做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种族中心主义。
因此,作者进一步认为,如果忽视历史,人类学也就与科学分道扬镳。这并不难理解:科学要求我们对经验事实进行大量观察,要求我们广泛搜集证据,并且在比较中挖掘一些普适性的法则、规律。而在人类学研究中,缺乏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就缺了相当一部分的数据。数据不完整,结论又谈何普遍性、科学性?光是从数据完整性的角度看,忽视历史的人类学已然与科学背道而驰。
三
接着,埃文斯-普理查德谈了谈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区别。从时间跨度看,似乎人类学家只关注某个现象在特定时点的状况,而历史学家则关注某个现象一直以来的发展。比如,要研究皇室在英国公共生活的地位。人类学家一般只关注当代或者某个时期。而历史学家可能会追溯几个世纪的王权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以不同的角度获取数据,又以不同的方式写作。当然,作者也指出,要更好地理解某个时期皇室的地位,最好和其他时期进行比较。因此,我们是否使用历史数据,取决于它对我们的研究问题是否有意义。
而从研究的时间导向(orientation)看,似乎历史学家是正序研究——从古至今,由远及近;而人类学家是倒序研究——由今溯古,由近及远。比如,要研究英国议会历史,历史学家会从起源追随到当下,但他们不会到具体的议会中观察。他们甚至认为这不利于自身的研究。他们是以“过去”解释“当下”。人类学家会怎么做呢?他们大概率会亲自到议会大厅,研究今天的议会生活:议事过程、党派类别、压力群体、机构组织、成员的阶层/宗教分布等等,在掌握这些信息以后,试着解释过去的一些发展阶段。在我看来,他的例子并不那么恰当。人类学家的研究顺序并非真的如此一板一眼。到底采取哪种顺序,取决于他的研究问题。也许作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后文说:这种区分是虚幻的(illusory)。
从研究目标看,人类学家的目标是找出一些恒定的特征、关联以及重复发生的事情,并试图从中抽象出一些普遍的东西,而不是像历史学家那样用起源/前因来解释当下。
其实,从作者讲述的这些区别来看,我们很难说人类学和历史学有什么显著的区别,他的论述反而说明了两者往往如纱线般交织在一起。他对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区分看似是无效的,但这正是他最终的意图:我们没必要对两者作一个明确的区分。它们都是社会科学/社会研究的分支,都是为了研究社会而存在的。最佳的出路,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也就是将历史学的历时性取向与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共时性取向结合起来。
四
假设我们已经有了两者结合的意识,但在操作层面上,我们该怎么做呢?作者并没有在后文给我们指出一条具体的结合路径。不过,在他前文的论述中,我们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他在论述人类学研究忽视历史的后果时指出,人类学家在研究时可以这样发问:
为何有的社会有着丰富的历史,而有的社会却“历史”贫乏? 在一个社会中,哪些事件是值得铭记的?这些事件与具体的社会关系、权利有何关联? 人们采用哪些助记词来代表一个地区的景观地貌、社会结构、物质文化的特点? 环境因素对一个民族的传统以及人们的时间感有何影响?
这些发问在其著作《努尔人》已经有所体现——正如他考察努尔人所处的生态环境对其生计方式的影响,考察努尔人的取名习惯,考察努尔人对牛的兴趣。他的努力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引发了“Nuerosis”(谐音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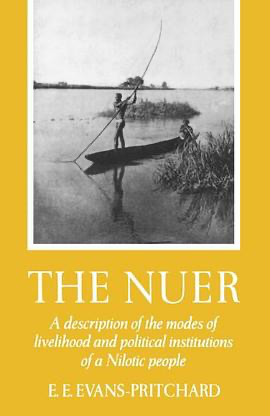
另外,我们也可以借助历史,对一些习以为常的假设进行检验。比如作者在文章中提到要检验一些功能主义者的基本假设: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名为“社会”的实体?结构真的存在吗?当我们追溯历史并加以比较分析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些基本假设有了更多的认识。总之,他向我们展示了历史之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除了对功能主义进行了历时性视角的补充、推动方法论层面的完善,这篇文章更大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启发我们,挖掘出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切的发问都是从比较开始的。一种现象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好奇,一般都是因为它“起了变化”,或是与过往的情况/体验/经验不同。而关注历史,也就促使我们从今昔对比中挖掘问题。比如近年来出现了“抱团养老”,那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发问:以前人们如何养老?以前有“抱团”吗?为什么这几年会出现“抱团”,它为什么会失败了?
从这些朴素的问题出发,我们的研究得以变得清晰明了。
可以说,埃文斯-普理查德的这篇演说,让人类学者开始将“历史”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分析范畴,成为民族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历史人类学“也失去了像经济人类学或政治和法律人类学那样成为一个分支学科(阶段性)的必要性了。
复旦人类学 方志伟 推荐
胡潇月 编辑

